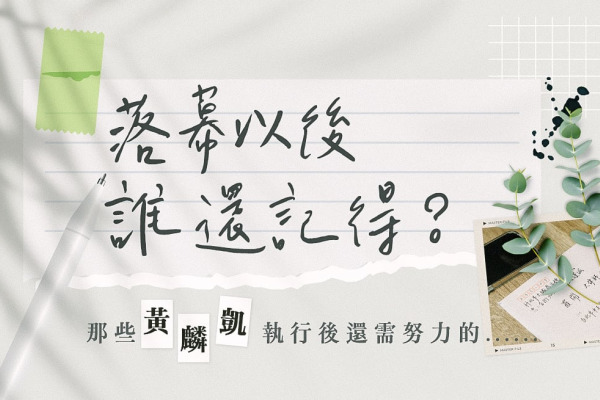電子報
廢死聯盟說的話,是為《廢話》。
在2010年的死刑爭議裡,我們受封為「最邪惡的人權團體」,我們的主張,看起來確實狗吠火車,所以《廢話》也就是「吠話」。知其不可而吠之,汪汪!《廢話電子報》於2012年2月首次發刊,每個月發行的廢話電子報是廢死聯盟實踐與社會溝通的方式之一,我們期許自己用淺白、易懂的文字,透過定期的發刊,持續跟社會對話。
憲判8,然後呢?—專訪錢建榮律師、羅秉成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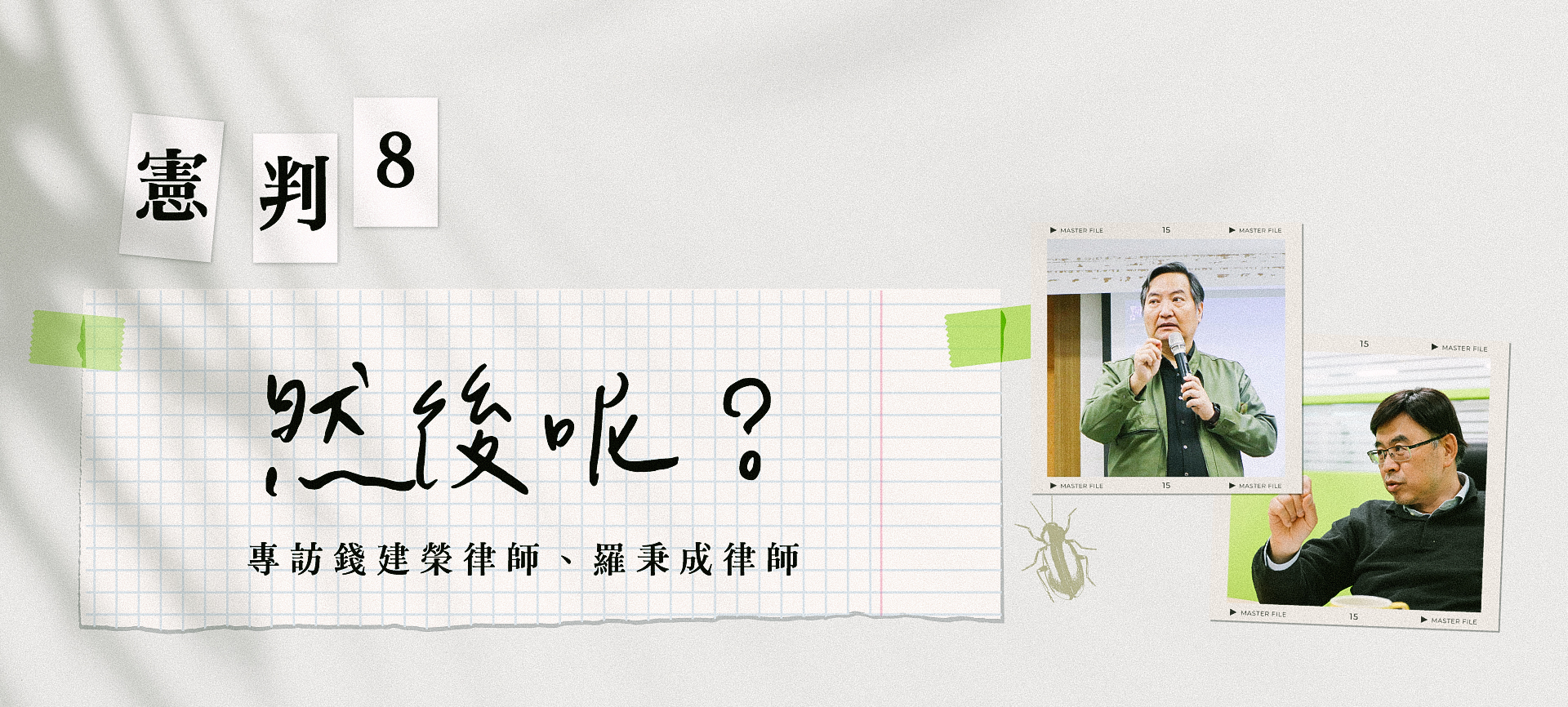
文/林安冬(律師、廢話電子報特約記者)
前 言
在台灣,死刑議題一直是公眾熱議的焦點。尤其是在近期,黃麟凱案的死刑執行,引發了社會各界對死刑的合法性與執行程序的深刻討論。2025年2月25日下午,我們有幸採訪了兩位資深律師——羅秉成律師與錢建榮律師,訪談了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下稱「憲判8」)後的死刑難題。
壹、黃麟凱的槍決是違法的執行
| 問:今年1月16日法務部執行黃麟凱的死刑判決,法務部次長黃謀信並於當日執行後的記者會表示,「本案刑事程序之進行,符合憲法判決所揭示的確定之終局判決,經辯護人到庭辯護、經過言詞辯論,合議庭法庭法官一致決以及其他《憲法》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保障。」(公視新聞),等同於法務部在檢察總長尚未提起非常上訴、最高法院也未及審理的狀況下,自行審查死刑個案是否符合113憲判8的要求,請問兩位律師對此一程序的看法為何? |
錢建榮律師
 (攝影/張馥如)
(攝影/張馥如)
首先要知道的是,死刑執行的流程必須是檢察總長確定沒有提非常上訴的事由後,才能送「死刑執行審議小組」,最後由法務部部長決定。
至於總長如何判斷有無非常上訴的事由?憲判8對於死刑判決,提出了1個實體要求、7個程序要求;其中,「最嚴重犯罪才可以判死刑」的實體要求(主文10),是法院才能決定,而不是檢察官乃至於檢察總長可以判斷的事項。但黃麟凱在執行死刑前,法院根本沒有進行上述的決定,因為在法務部決定執行時,律師還沒遞狀、總長也也沒向法院聲請。
此外,從憲判8的主文9、13來看,本次執行的違法之處也不只一點。主文9要求,必須評估被告是否具備心智缺陷而影響受刑能力;但本次執行那麼匆促的情況下,黃麟凱也沒有經過鑑定。
主文13則是要求「確定終局判決」必須經合議庭一致決。但有疑問的是,「確定終局判決」是否有包括二審判決的可能?本案的三審,是以「上訴無理由」而駁回的實體判決,因此總長就認為「確定終局判決」是三審判決,而僅詢問最高法院該判決有無一致決。然而,不要忘了最高法院的事實認定部分,是以二審判決為基礎的!因為最高法院只能依二審認定的事實進行法律審,不會重新認定事實,所以把二、三審合併觀察才會是一個完整的判決。在死刑案件中,二審法院作為最後事實審,合議庭的三位法官有沒有在事實認定上達成一致,就會非常關鍵。
這個看法當然也是有依據的。最高法院91年度第8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有討論一個法律問題,檢察官在執行死刑前發現,該案的二審辯護人於辯護時都只說:「辯護意旨如辯護狀所載。」但事實是,律師根本沒有提出辯護狀。這顯然是未受實質有效辯護的情形,構成《刑事訴訟法》第379條判決違背法令的情形。因此,這個案件就回到最高法院討論,爭執的點在於:除了原本的三審判決要撤銷以外,二審判決的違法要不要一併處理?結論上來說,最高法院在後續的處理中,把二審、三審判決都認定是違法,就印證了我上面說的,二、三審必須合併觀察,才形成一個完整的「確定終局判決」。
但我們現在遇到的狀況是,檢察總長不去思考、處理這些問題,在違法的情況下,急急忙忙地就把人拖去槍斃了。
羅秉成律師

我在與林慈偉、陳思妤合寫的〈論憲法判決後的特別非常上訴救濟──以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為例〉一文中有提到,大法官賦予黃麟凱在內的聲請人,有主文第10項至第14項的「特別非常上訴事由」。
與《刑事訴訟法》一般的非上事由不同,一般非上當事人沒有「聲請權」可言,總長不受理就沒有權利進行救濟;但是,憲法訴訟制度對於個案聲請人有例外的溯及效果。因此,憲判8雖然是寫「個案可以向總長請求(或總長可依職權)」提出非常上訴」,但總長應當只能進行「形式審查」。例如,就「第三審是否經強制辯護及言詞辯論?」、「確定終局裁判是否為一致決?」等部分,是形式上就可以判斷。
然而,「是否屬於情節最嚴重之罪?」、「是否有心智缺陷?」則是必須實質審查的要件,不應由總長做審查。否則,就會變成總長而非法院建立死刑的執行基準。比如黃麟凱的律師最後有及時提出非上的請求,主張黃案不符合情節最嚴重之罪,卻未經法庭調查、辯論,片面地由總長判斷,並非大法官的本意。憲判8的本意,應是要求總長謙抑其非上的審查權,透過法院的審理程序重新判斷案件是否符合憲判8的「情節最嚴重」要件,否則即會對當事人訴訟權有嚴重影響。
貳、執行死刑對其他死刑案件的影響
| 問:就政治及司法兩個層面而言,此次執行,對於113憲判8其餘36位死刑定讞的聲請人來說,是否可能有任何影響? |
錢建榮律師
在司法層面上,我認為針對本次違法的執行,應該要提出「確認執行違法之訴」,因為如果我們不能確定這次執行是違法的,總長就會認為自己有權跳過法院,直接審查包括「情節最嚴重」的憲判8要件。政治層面上,總長跟總統等於不用理會憲判8設下的法律要件,大法官雖然透過司法限制了行政的執行權,但法務部長卻不予理會,可以說是藐視司法權、輕視憲法規範。我也認為本次的執行,不能反面推論總長對其他36位聲請人提起非上的機率會比較高,因為總長目前認為自己有權力審查、判斷憲判8的要件。
另一方面,也有人推論本次執行安排在年前的原因是,國民黨想把公投綁大選修法回來,再把死刑公投綁大選,所以民進黨政府就殺一個人來因應。就社會層面而言,依我的印象,前總統蔡英文執行死刑後,某間速食業者剛好有大特價促銷的活動,當時的新聞都只有報特價的事,沒有關注死刑的執行。可以見得,執行死刑這個行動並無法主導民意。
羅秉成律師
如果說,我們推測法務部檢視了全部37個案件,只認為黃麟凱案符合憲判8的要件,才加以執行。反過來說,或許能正面地理解其他36個案件皆會提起非常上訴。但在黃案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總長認為自己對於「情節最嚴重之罪」有實質審查權,所以即便總長對其他個案提起非上,也有可能不會主張此項理由。而最高法院因為有類似「不告不理」的原則,因此若總長不主張這個要件,最高法院就不會在個案中重新審查是否符合「情節最嚴重」,讓非上的強度大大削弱,變成只有處理程序面的審理。
政治上,賴政府有可能在某種政治氛圍下,進行內部討論後進行執行死刑的政治決定,但民心都是一時的,可以說賴政府透過本次執行,只傳遞了一種訊息:「民意對憲判8不滿意」。
對個案救濟來說,仍應回到法律攻防。本次執行跟之前歷次執行都一樣,是突襲性的執行,在事前律師和家屬都不知情,並沒有給予當事人合理適當的時間向親友告別,且刻意迴避個案的救濟,已達不人道的地步,這一點也有違憲之虞。
後續總長在另外36個案件中,有無以「情節最嚴重」為理由提起非上,很值得觀察。因為律師方面,全數案件應該都有主張這個理由,然而目前已知總長是持非常保守的見解,可能會自己認定有些案件並沒有這一非常上訴事由。
參、憲判8對司法實務的影響:支持死刑還是限縮死刑?
錢建榮律師
我認為,當前最高法院對於死刑的適用已趨於謹慎,近年來幾乎沒有新的死刑判決定讞。憲判8的內容可以說是重複最高法院原本的見解,甚至有些倒退,例如劉志明案中,最高法院加上了「非計畫性」的要件;而陳彥翔案則因為行為人是「間接故意」,最高法院對此早已形成穩定見解,不容許判處死刑。
然而,在憲判8作成後,一、二審法院卻反而可能會因此鬆動,出現更多死刑判決。憲判8的發佈,某種程度上使得死刑案件的審理變得更加複雜,一、二審法官也可能有一種不負責任的想法,認為之後還有上訴的救濟,就先判處死刑。另一方面,一、二審的判決其實不是跟著憲法法庭走的,而是跟著「最高法院」走的,所以下級審法院應該尚在觀望最高法院的見解會否因為憲判8而鬆動。
羅秉成律師
我認為憲判8後的個案發展值得再觀察,目前案件量還不夠,論斷來說太早。但理論上來講,特定政黨將憲判8稱呼為「實質廢死」,完全是一種政治操作,因為黃案的執行和死刑維持的判決都已經堵住這些人的說法。但是,對於實際進行中個案的影響,以維持死刑的案件來說,目前因為都尚未確定,還需要觀察上訴後最高法院的見解才能判斷。
對最高法院而言,除了一致決以外,憲判8對法律見解的影響不大,因為憲判8的要件都是最高法院已經在做的。但憲判8已經作成,下一個釋憲案遙遙無期,若在現實層面上無法減少死刑的立法、執行和判決,憲判8反而就會是廢死運動的反挫,等於披著「超級正當程序」的外衣,加速死刑的執行,但相關風險例如冤錯案仍是存在的。
肆、死刑的「公正應報」與「嚇阻力」——死刑的正當性基礎何在?
|
問:近期高雄發生連續殺人分屍的案件震驚社會,警方透過監視器畫面還原時間軸,其中第二位被害人遭到殺害的時間點,似乎就是在法務部執行槍決的隔天(1月17日,TVBS新聞);且根據新聞報導,高雄市警察局長林炎田在警詢時,曾經告誡嫌疑人:「犯下泯滅人性的罪,最後會被槍斃」,嫌疑人卻反嗆「你槍斃我啊」(UDN新聞)。從這個案件看來,執行死刑似乎對於殺人案的「嚇阻力」有限,但113憲判8的理由書說明:「於我國歷史及社會脈絡下,得認公正應報及嚇阻侵害生命法益之重大犯罪,於目前仍為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是系爭規定一至四有關以死刑為最重本刑之規定部分,其目的尚屬合憲。」、「死刑之制裁手段,始為達成公正應報及嚇阻侵害生命法益之重大犯罪之目的所必要之手段。」若排除了「嚇阻力」,似乎只剩「公正應報」可以作為死刑制度的正當目的,而事實上黃麟凱案的被害人家屬也在執行後表示欣慰(自由時報新聞)。 請問兩位律師認為,「公正應報」是否足以作為死刑的正當性基礎?
|
錢建榮律師
關於嚇阻力的問題,這其實是無法檢驗的事項。在刑事個案的審判上,仍應該回歸「罪疑惟輕原則」進行有利於被告的推定,而不是拿個案被告的刑度來嚇阻社會。
「公正應報」的概念與「報復」不同,死刑是一種過度的「報復」,它也傷害了死刑犯的家屬,況且一命永遠也抵不了一命。「報復」絕不是刑罰的理念,憲判8還直接說特別預防在死刑沒有適用,但公正應報應該是特別預防的概念下才有意義的。
如果說,死刑就是回應了一般人或被害人對刑法「正義」的想像,那我們又該怎麼辦呢?其實,這個想像是不穩固的,它是我們長久的文化形塑出對於死刑的「習慣」,而不是普世的價值。歐洲廢死其實也只是幾十年前的事而已,年輕一輩習慣了沒有死刑的社會,他們會覺得過往的死刑很殘忍。法律其實可當作是一種導正文化的制度,例如同婚已經是現在非常自然的事情,這也是因為制度引導社會文化的改變。「人性」有殘暴的一面,而法律就是有必要去改善、糾正這一面。
羅秉成律師
我在〈因苦衷而折衷,因自欺而自棄〉一文中有提到:「憲判8號是帶有政治後果考量的妥協性判決,主文第一項死刑合憲的主要理由是:『…選擇死刑為其最重本刑…並期發揮刑罰之嚇阻功能,以減少犯罪』的立法功能『為我國多數人民之法感情所支持』,且『於我國歷史及社會脈絡下,得認公正應報及嚇阻侵害生命法益之重大犯罪,於目前仍為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詳參判決第67、68段)等語,明白向台灣『目前』的『多數民意』和『歷史社會脈絡』妥協,而對此難以服人的牽強理由,則另以提高死刑判決須合乎『最嚴密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同時宣告多項死刑訴訟程序規定違憲(詳參判決主文第3、4、5、6項),試圖加以平衡調和死刑的嚴峻性。」
其實,「公正應報」和「嚇阻」以及「歷史脈絡」都是站在民意的角度,但人權本就有「抗多數」的性質。憲判8的理由從眾媚俗,法律工作者、人權工作者不應落入這個窠臼。已經有許多實證研究指出,重刑不會產生嚇阻效果,不僅沒有辦法嚇阻,甚至可能讓犯罪者誤以為會認為殺一個賺一個。早年陳進興案就是如此,因為陳可預見自己一定會被判死刑,所以他在逃亡的過程中仍然為非作歹、手段兇殘沒有節制。通案來說,犯人在下手時,很難想到自己會被判死刑或考慮法律後果。
回到「公正應報」的問題,我們或許可以問大法官:「應報」如何「公正」?以眼還眼的正義觀不是現代法治社會應走的路,而大法官也沒說明應報的公正性與界限到底何在。
如果說,死刑制度就是一般人或被害人對刑法「正義」的想像,那這就是廢死運動一直以來最大的的崁──這就是與一般人的距離,很難三言兩語說清。尤其現在網路世代、意見極化的背景下更惡化了,理性討論的空間很小,很難好好坐下來談。對話是零碎、片段的。
歐洲國家也曾經面臨這樣的難題,一般公眾與人權工作者的距離要如何填補?我覺得目前可能還沒有很好的答案,但網路作為中性的媒介、工具,其中的討論有沒有可能有效擴散反對死刑的理念?《慷慨的感染力》一書中,提到網路的正面作用,例如疫情下為善的力量的感染力也很強大,因此,不要畏懼網路,而應擅用它,讓善的力量可以在網路上和惡的力量競逐。
公眾的對話仍應持續,被害人家屬的部分,死刑是最廉價的滿足,但社會也可能造成被害人的壓力,因為一般人都在呼籲應該死刑,記者不應去追問被害人家屬是否認為犯人應判處死刑,否則「不認為要判死刑的被害人家屬」也會變成群眾認為另類的加害者。對一般人來說,比較容易站在被害人的角度。但就廢死理念對一般人的影響,樂觀來看,仍有可能改變。以我的經驗來說,身邊的親友雖不容易支持廢死,但至少會對死刑制度產生懷疑。我會用提問、反問的方式思考(例如死刑冤案江國慶案),讓大家對死刑產生懷疑,而非直接從廢死論點出發,這是一種有效的作法。
伍、有兩成的台灣人堅定支持廢死!
|
問:在本次執行之後,兩位律師作為廢死運動的人權工作,有沒有想對社會大眾說的話? |
錢建榮律師
我希望社會大眾不要放棄思考,要一再去反思現行的社會制度,對國家公權力抱持警戒心。國家是會做壞事的,公權力可能為惡,民眾要時時反思社會制度的合理性。
就廢死運動來看,比較可以期待的是司法菁英,而非行政權或立法權。廢死運動的下一步應該是下一次釋憲。憲判8雖然是一個合憲判決,但它並沒有直接針對刑法第33條「死刑作為一種主刑」的規定解釋為合憲,下一次釋憲可能可以以此著手。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行政端要停止死刑的執行。以韓國為例,他們是依賴行政權實質廢死,但韓國法律上死刑仍合憲。
我的有生之年可能等不到死刑制度再一次作為憲法法庭討論的題目。台灣一定有一天會廢死,但樂觀來說至少還要二、三十年。
羅秉成律師
我認為,最佳的情勢還是在民意支持下廢除死刑。雖然大眾素養的提升會很緩慢,可能要一、兩百年的時間,但是我們不要放棄,還是可以嘗試透過公眾對話讓民意逆轉。
我應該是看不到台灣達成廢死了,但在對話的不斷累積下,我們不要放棄改變民眾看法,要讓中間立場的人靠攏過來。現在的困境是兩頭不到岸,廢也不是、不廢也不是。彌足珍貴的是,雖然穩定有八成的民眾支持死刑,但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反過來可以看到有兩成的人也堅定地支持廢死。其實就數量上來說,不是也很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