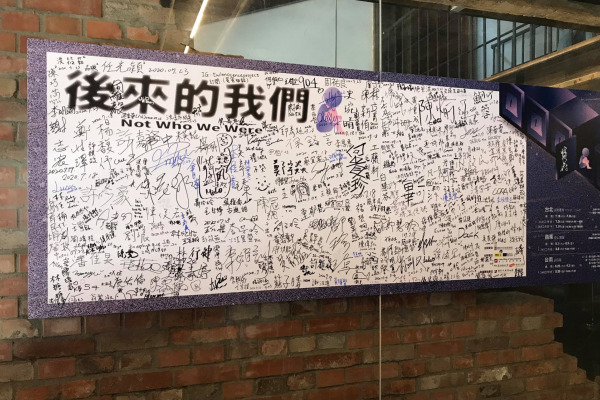先做對的事—訪《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導演李家驊、佳映娛樂負責人劉嘉明
文/吳奕靜(廢死聯盟執行秘書)
在《我的兒子是死刑犯》上映前夕,廢話電子報團隊來到佳映娛樂的辦公室,入門左手邊便是,克勞蒂亞·卡蒂納(Claudia Cardinale)手足舞蹈迎接著,那是第70屆坎城影展視覺海報,再向前看去,白牆上有手繪的羅丹頭像,玻璃櫃中散落著各式各樣的電影文宣、攝影技術相關的作品。

誰會想談死刑犯的議題?
2005年創生「佳映娛樂」的劉嘉明,大家稱呼他James。有著軍法官父親的James,雖然自小受到嚴格的教育,卻也曾看見父親充滿人性、開明的一面。在他的印象中,父親手上有許多生命因此留下,而那同時也是他對電影有了更多接觸的起源。
當年父親在金門的駕駛兵,是一位十幾歲從廣東逃亡的孩子,被送到軍法審判,父親卻將他留下,因而成為了父親的駕駛兵,於是在周末、年節這位無依無靠的駕駛兵都會和他們家一起聚餐,父親也經常找他在湖北的老鄉來一同吃飯,照顧比他年幼的後輩,這是軍人外省家庭的生活方式。駕駛兵吃過午飯後不方便在他們家中休息,便會帶著年幼的James一起去電影院,「他在電影院休息,我在看電影。」這是James與電影最初的緣分。
「我是被好萊塢養大的小孩。」廣告系畢業的導演李家驊不諱言。他對紀錄片開始感興趣,是大三時老師在課堂上播放紀錄片,他才發現,原來電影可以這樣拍;後來考上台南藝術大學,一步一步往拍片之路前進。從小就想要拍電影的他,有打工賺錢以來就把最多的錢花在電影院,什麼電影都看。
兩人因為《夢想續航》結緣,家驊第一次看到James時,內心還想著「天啊!這個人看起來好嚴肅!」直到後來合作才完全改觀。家驊曾經跟許多不同電影公司合作過,也因為這些經驗讓他對電影公司相對有戒心。但剛開始李中旺導演(和James同一個眷村長大)牽線,他看到《夢想續航》主題時,還問李導說:「這個公司是哪裡有問題?」
很少人像James這樣,政大新聞系畢業,從片場器材出租公司的黑手開始,也到中國做過器材出租的生意,原先想自己拍電影卻跌了一跤,而後又進入劇場工作三、四年,期間寫了劇本也演了舞台劇,後來終於拍了電影...... 再到專門放法國藝術電影的電影台工作,才是現在的電影製作公司,將電影產業從基層到統籌全都摸索過一遍。「我可能很沒品,因為我不挑(工作)的,只要在電影的產業裡面。」James惡趣味地說。但如果不是這些歷練,他認為自己是完全無法理解表演的,那是活生生的刺激與現場震撼。從當時算到現在也已經三十年,James未曾離開過電影產業工作。
這個電影不需要有特殊之處,它需要被更多人看到
關於《我的兒子是死刑犯》,James表示,不能將一個談死刑的電影,用商業發行的角度去談,以商業發行的角度要「精采」是很容易的,這正是《我的兒子是死刑犯》的難處。無論觀眾支持什麼,表達一個意見是重要的,同時作為一個發行商,維護表達的權利更是重要的。《我的兒子是死刑犯》讓人更了解死刑是怎麼一回事,至少它已經建立一種討論的可能性。
「人永遠在作品之前。這是我一直記得自己在南藝接受到的訓練。」家驊也說,如果片子不好,他樂於接受這個結果,因為這是他一直堅守的底線。也是整個剪片過程中他與剪片師討論的,哀矜勿喜。無論《我的兒子是死刑犯》最終能獲得多少獎項與掌聲,團隊都會記得這是活生生的生命故事。即使在過程中訪問過許多受訪者最終是不能使用的,或者與政府部門的溝通反覆,但他們盡力做出了現在的樣貌。
活一天,就要做一天事

「生命的創造不是人,而是造物主。每一個生命都相對是一種生產力,他必須帶給這個社會一個正面的東西,每個人都有一個能力去貢獻這個社會。當生命被拿走時,貢獻就不見了,但如果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有貢獻的可能性,那麼奪走一個生命,也就喪失了一種貢獻的機會。」James對於生命的理解是如此的。他也提到,我們經常看電影會認為片中的死刑只是錯覺,不是真實,但若將死刑的經驗放回日常生活的情境中,便有許多「穿幫」。James認為,人類應該可以找到更好的方式來應對人類的犯罪,而對一個人的終極懲罰也應該是這個人必須繼續對社會貢獻,而非消極奪取生命,他笑稱自己很社會主義,但也許是受到母親的影響,活一天,你就要做一天事。

家驊則說,自己三十歲以前其實支持死刑。直到被蔡崇隆導演找去拍《島國殺人紀事3:自由的滋味》了解蘇建和案以後才改觀,認知到原來法律會殺錯人,但是他轉念一想,怎麼樣才叫做「殺對人」?發現無論如何政府都不會「殺對人」,因此越來越不信任司法制度,轉為希望廢除死刑。家驊也理解許多人不支持廢死,因為這個社會需要安定感。只是很遺憾地,在多數亞洲國家的文化中,這種安定感來自威權秩序的遺留。「我們對個體之間的信心是不夠的,於是我們就很信任國家強制力的運作,然而大家卻遺忘了國家的機制是有問題的、會出錯的,如果這個機制並不值得信任,我們要如何去倚賴一個充滿漏洞的制度?」家驊表示。
James也分享自己看過的一些片子。比如劉吉雄的《次日死者》拍攝屠宰場的一日,全片沒有對白,拍攝豬到屠宰場,分類、銷售、喊價、屠宰的程序,結束後拜拜,這部片在告訴我們什麼?另一個問題是,那些施暴的人是如何思索生命?也許對殺人的人而言,他的生長過程中對生命的思考就是很匱乏且不足的,那麼他所能想到的解決方式固然也就十分少。如果人是有感情的,我們應該如何理解發生的事?如何去接受?
因為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們就去做吧!
佳映娛樂剛成立時,有位股東邀James一起去看一組太陽能車隊,他們想要出國比賽,但還籌不到足夠的款項。「那次的經驗就是看到一個大學教授和一群學生在工廠裡面,大學教授非常盡責,而這些高學歷的學生們在炎熱的天氣下毫不在意地專注在太陽能車身上。」於是他感受到原來台灣在科技技術領域能夠維持現有的局面,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人在,而那次就和李中旺導演合作拍攝了紀錄片《夢想無限》。十年後,James感念公司能夠持續經營,想到《夢想無限》和李中旺導演討論後,決定找新世代導演—李家驊來進行《夢想續航》的拍攝,紀錄太陽能車隊成員十年後的境況,不只是夢想的意義,也是一種傳承、接續。James說,與家驊的合作沒有什麼刻意的媒合「有時候不是說這個緣分多深,而是有人願意一起來想辦法做好這份工作,我覺得我們非常享受這種工作方法。」
「每一部影片都是一個教育的過程,透過這些電影教育自己,了解這個世界不同的人在做什麼。」James的視角,也充分說明了佳映的選擇。
「佳映娛樂」畢竟是一個營利事業,但是在營利的必要背後其實有很多不同方式進行,James說,總是希望多少跟自己當初學新聞有一些關聯,對於社會議題的許多不同想法,作為一個製作同時也是發行公司,若能找到需要被社會討論、注意的議題,佳映娛樂可以做這樣的選擇。「我總是希望說先做一件對的事情,然後再讓它賺錢。而不是先去想賺錢然後再來做對的事情。」這樣的理念深深影響了佳映選擇做的電影、與什麼樣的導演合作。
近年來美國、日本、韓國也經常推出與社會議題相關優質的影視作品,對此家驊表示,影視作品通常總是前進得比整個社會的接受度慢一點點。但我們的社會其實有在前進,這件事情反映在影視作品上面是可以得知的,如《我們與惡的距離》等作品,台灣確實越來越敢去接觸我們覺得比較敏感的東西。他也認為,James很大膽,在很敏感的時候就把賈樟柯的作品帶入台灣進來,他也從來沒有聽過James說什麼樣的題材因為不能進中國而無法發行。

兩人最近也有合作一部新作品,談一位台灣教練帶著孩子們去參加現代五項的賽事。起源於James多年前去歐洲參加柏林影展,在飛機上遇到這位台灣教練,他說自己只會體育不會念書,很早就被教育體制放棄的小孩,是體育救了他。他說:「台灣的教育都是花很多心力、資源將90分的小孩變成92分,可是大家都不知道一樣的資源只要拿一點點過來,就可以讓很多30分的小孩變成60分。他就是要做這樣的事情。」而當家驊接觸到這位教練時,問他如何挑選要帶的孩子,他答:「怎麼挑?別人不要的小孩我都要。」於是這部新片便成行了。
本著投入一個夢想之心實踐初衷,即使最終未必能夠到達彼方,卻證實了這個世界的希望存在,「因為還有人願意付出」這是James想要傳達給社會的。導演李家驊也在紀錄片領域中以相對節制的方式,拓展出我們可以共同面對、思考死刑的可能。《我的兒子是死刑犯》也許沉重,也許一點也不「充滿希望」,卻是被帶著這樣的期許生成的真誠之作。也邀請大家,一同進入電影院,這次,我們見證著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