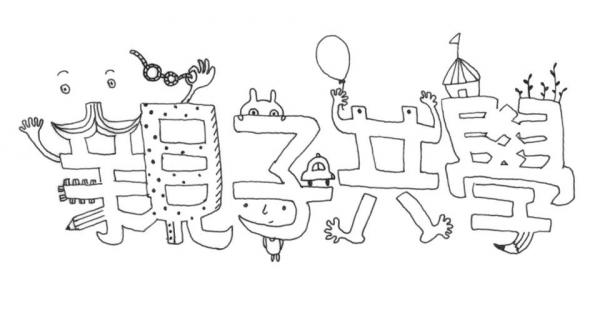倡議與行動
這裡會有廢死聯盟的新聞稿及倡議行動。
失去了一個孩子以後: 找到面對未知仍給出信任、連繫彼此的勇氣
失去了一個孩子以後:
找到面對未知仍給出信任、連繫彼此的勇氣
文/陳亭亘(諮商心理師)
※重要提醒:本文可能有些描述會令人不舒服,請斟酌閱覽,並理解作者並沒有想汙名化任何族群的意思,只是想描述一個現象。
老實說,當小燈泡過世以後,我聽過不只一次「這個媽媽太冷靜了,一定哪裡有問題」、「你怎麼知道她不是因為家裡小孩太多,少一個也無所謂…」云云。
雖然不是不能理解那種旁觀者的困惑,但聽到這種論點的時候,總是不禁讓我覺得「這個推論也太險惡了吧」,我總是相信,應該沒有一個母親會對自己懷胎十月、辛苦養育的孩子動這樣的念頭,但我仍然對於是什麼讓這對父母親能做到這樣的超然,對生命、對失去這麼坦然不太理解。
直到我到了一個共學團去分享,才理解到或許那就是他們每天都練習著的事─一件直指生命本質的事。
家長們試著面對未知,試著面對內在的擔憂與恐懼,試著給出允許,試著相信孩子會有自己的能力,試著相信自己不需要控制一切事情,也試著了解自己終究無法控制每一件事,在自己的內在反覆的拉扯,放手、控制、放手、控制、放手、試著放手,然後試著讓孩子長出自己、認識環境、擁有動能。
這樣的「放手」、「開放」、與「討論」顯然都是罕見的。
一來,這必須建立在「父母親內心有餘裕」的情況下,但這個忙碌而低薪的社會,要有餘裕需要一點經濟基礎;二來,這必須建立在「父母親願意壓抑,並處理自己的情緒」,面對孩子所將遭遇的各種未知,剪除各種可能遭遇的困境以迴避自己內心的焦慮,總是比協助孩子面對各種未知、進行挑戰要來得容易。
所以不難理解,面對潛在的兒童傷害事件,人們總是感覺憤怒、希望加強各種控制、除去惡人、唯一死刑、糾眾毆打犯人,希望剪除所有可能導致的傷害,好讓我們摯愛的人能安然,也讓自己能感到安然。
但,這樣的剪除究竟是為了「羞辱的愉悅」、「眼不見為淨」或是「不再製造下一個犯人」?
參與的一個媽媽認真的問著「有一種說法說反社會人格的人個性……,所以如果在監獄裡終身監禁,他搞不好會跟其他反社會人格的人氣味相投,交到在外面交不到的朋友,在監獄裡面過得很快樂」,仔細說來,這真是個有趣的問題,面對犯罪者,我們似乎總是期待他們「過得很不好」才可以,而不是「不要造成對社會的危害」?
參與的另外一個媽媽告訴我「之前的傷害事件發生後,她們要出來共學變得更加困難,先生會期待她們找密閉的空間,然後要通知警察到場保護」,但這樣的方式似乎就違反了她們的初衷,不違反初衷又會違反了先生的意願,造成關係上的緊張。
我看著那些個在媽媽的背上、媽媽的懷裡情緒安穩的孩子,一個媽媽告訴我「或許是因為有讓他們玩到滿足點吧,所以就會甘願,情緒也比較穩定」,放手帶來的孩子的安穩,與控制帶來的父母親情緒放鬆,是一個反覆上演的拉鋸。
一個媽媽說,「其實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怎麼跟我的孩子提這件事,總是覺得很難把自己安頓好,怕講得不好反而引發孩子焦慮」;另外一個媽媽說「我跟孩子提過我會想辦法保護他,但他還是害怕得哇哇大叫,…到後來我發現只有讓他找到自己的力量,想像可以有一個安全的遮罩保護他,他才好一點」,其實家長們都知道「世界上沒有萬無一失的事」,每個人都只能盡力,但卻不知道會有什麼後果,跟自己能不能承受。
這,其實就是生命的一體兩面,堅韌與脆弱。
面對接二連三的社會傷害事件,我們可以選擇想盡辦法維護自己家人的安危,並驅逐那所有讓我們感到不安的人事物,但,我們也可以選擇想盡辦法增加與他人的連結,讓那些失落的、孤單的人不至於走到最後一步,也讓身邊的人成為彼此支持的那張網。
沒有證據的信任需要勇氣,迴避脆弱而施加的控制往往讓社會集體變得更脆弱。
而我們,究竟該選擇怎麼一起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