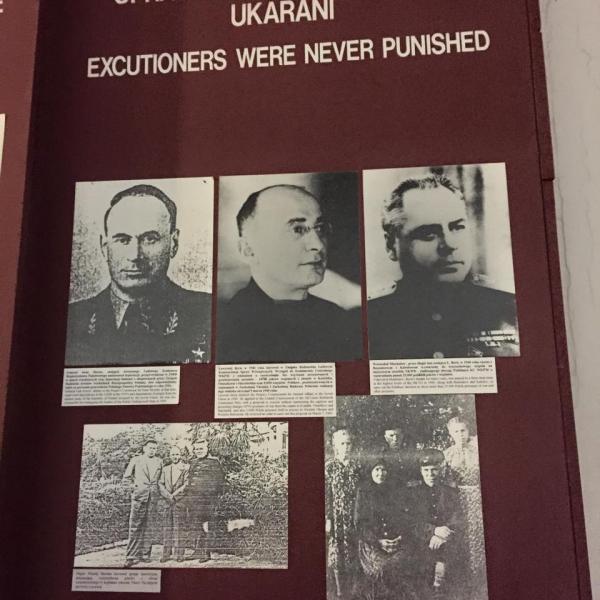倡議與行動
這裡會有廢死聯盟的新聞稿及倡議行動。
「死」型正義─專訪吳豪人
「死」型正義─專訪吳豪人
採訪撰稿/葉宇軒(廢話電子報記者)
死刑,當它做為政治的手段,活躍於政治舞台,會是怎樣一幅光景?
古往今來無數政權興替中,我們已經看得太多:誅除、肅清、屠戮、殘殺──對當權者而言,政敵、百姓、異議者乃至前朝遺民,在飽含政治算計的「依法行政」裡頭,取他們的性命,不過是一句話、甚至一個眼神的功夫。「死刑」的存在,正為了許多心懷不軌的執政者,開啟一扇方便之門,而我們引頸期盼透過完備法制能夠捍衛的正義,蕩然無存。
若說死刑與政治的關係,早是法政治學由來已久的命題,那麼「轉型正義與死刑,有什麼關係?」這恐怕就令不少人費解。因此,我們特別請教精研法學及人權思想的輔仁大學法律系吳豪人副教授,以平易近人的語言,淺顯易懂的舉例,和我們一同探究其間隱而不顯,其實唇亡齒寒的幽微關聯。
天上掉下來的「挪威傳奇」?
幾年前挪威極右翼的無差別殺人案,對台灣的廢死及反廢死陣營來說,都是一個重要的案件。挪威政府沒有因此恢復死刑,時常被廢死方用以宣傳其理念,對於反廢死方來說,挪威政府恐怕一夕間成為任用最多精神病患的政府單位。但是,吳豪人有話想說:「很多人其實沒有想過一個問題:這麼快樂、幸福、進步的北歐國家,有沒有轉型正義?」
時光回溯到二戰前後。當時,挪威被納粹占領,國內欣賞納粹主義者,也組織了納粹政黨,經由德國人的扶植奪得政權,在許多挪威人民眼裡,全是成群的「挪奸」,戰後,這些以挪威軍人與政治家維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 )為首、曾為納粹效命且為數眾多的挪威人,全數遭到監禁,面臨一系列嚴峻的審判。該魁儡政權的閣員幾乎全被判處死刑──畢竟二戰慘況記憶猶新,舉國悲憤。然而,其中有一人例外:魁儡政權的文化部長。
毫無差池的,這位文化部長一二審迎來了兩張死刑判決,戲劇化的翻轉,緣出本無關事證、在其他判例中幾乎是走過場的第三審:法律審。
在挪威的訴訟制度中,第三審並未強制被告出庭,然而被告若希望出庭,也未加禁止,於是,這位前文化部長便持之以恆的,每次開庭皆列席在場。每天每天,在合議庭的法官面前,他或坐或站,等待著判決。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穿著一套與眾人相似的西裝,既疲憊、悲傷又驚慌,很普通很普通的樣子。他具有律師資格,曾經做過律師,我們很容易想像他若未在戰中「失節」,現在庭中侷促不安的很可能會是另一個人,而他很可能正是那個被告的律師。每天每天,他準時出現,按耐著等待。最後,合議庭不知出於什麼原因,竟出人意表地判了無期徒刑,而沒有判死刑。
怎麼會這樣呢?
其中一位法官如此回憶:
「我實在沒有辦法在他身上看到那些,我們期待要看到的……那些怪物、怪獸、瘋狂的、殘暴的,擁有一顆邪惡的心的那些。全部沒有。」
「我一直看一直看,都只看到一個和我們一樣的,普通的人而已……」
「我們致力於清除這些骯髒的邪惡的東西,剛開始我們殺了好多好多人,叛徒、罪人,我們好氣好氣,但是殺到後來累了、疲倦了,氣也消了,再仔細一看,這些人跟我們有什麼不同呢?就真的非除掉不可嗎?他們跟我們有什麼差別?」
突然之間,手於是軟下去了。
「相對的,我又想到另一件事。」吳豪人喝了一口水,接著談起同時期的另一段歷史。
「二戰時,挪威居住許多挪威籍的猶太裔,納粹入侵以後,便把這些人都給帶走了。但是人數太多,公車、火車都不夠,怎麼辦才好呢?於是納粹政府便徵用一台一台計程車,一車一車載猶太人去港口搭船,轉運集中營。大家都知道這些人一旦離開,就回不來了。然而多數挪威人對此毫無反應。二戰結束後,紐倫堡大審期間,挪威人才像是突然驚覺:儘管他們對於被納粹佔領耿耿於懷,甚至大動肝火殺了許多「挪奸」,但是,面對納粹迫害猶太人這個更巨大的邪惡,他們當時毫無作為,甚至失憶至今。」
──若我們真是那麼可敬的民族,我們不能接受外國的統治,我們甚至嚴厲懲罰那些我們之中的叛徒,那我們為何可以眼睜睜看著這些無辜的生命在眼前被帶走,而不做任何表示?
「挪威人不是天生就比較文明。沒有那回事。」所有進步的思想,都是經過反省的:經過激情,也經過暴力。
當時紐倫堡大審的判決,幾乎無一例外地,全是死刑、死刑、死刑,彷彿我們要根除邪惡可怕的納粹思想,只能透過這樣澈底的趕盡殺絕──而這與納粹想透過種族清洗摒除「骯髒的猶太人」,其邏輯不正完全一致嗎?
最後,我們其實會發現,納粹分子絕非怪物。事實上,他們的存在完完全全棲息於人性一個可能的部分,我們急急忙忙想除掉那些「怪物」,不過是想藉此證明一件事:我的身上,沒有那種怪物。我們完全無法理解他們、我們跟他完完全全不同。
我們想證明這件事。然而,當真如此?
竊鉤者誅,竊國者……
轉型正義之所以存在,代表的正是在轉型之前,我們所面對的都是極為龐大的不義。不是一條兩條人命,而可能是數萬、數十萬條人命的滔天巨惡,它不但是有效率的、組織化的,更將許多人變成共犯,每個人負責一個殺人的環節。
「刑法的理論上,這些全是『共同正犯』,應同罪論處。」就納粹黨的暴行而言,不只那些執行死刑的軍兵、官員,理論上來說,整個國家的德國人,除非能證明自己曾抵抗納粹政權,否則依法都該判處死刑──但這顯然不實際,也太過殘酷。而且,經歷了這些極大的不義,往往舉國百廢待興,「依律當斬」的,全都是寶貴的勞動力,有人甚至是某些領域的菁英,除了死刑,他們的贖罪還有沒有其他可能?但他們又是這麼恐怖的罪人……
回答這個兩難的,是魁儡政權的文化部長所暴露的關鍵事實:那些我們以為三頭六臂的邪惡,都只是再平凡不過的人。於是我們伸出的手指,便再沒有辦法伸直。
如果我們身上都不帶有任何一點「怪物」的影子,我們又如何在別人的身上,看到怪物?就如漢娜鄂蘭對艾希曼的側寫──她再沒有看過比他更平凡更無聊的人了,但他卻負責了那六百萬條生命的消逝。那樣的瘋狂並非來自於艾希曼本身,而是整個世界的歇斯底里,正好在他手下集約的發生。那我們又該如何罪咎其身?
轉型正義的核心,是「不再發生(never again)」,是要去追問那些龐大到我們幾乎難以想像的罪惡,真正的原因,而非處決首謀,便天真的認為事件告終,never again。那些罪惡至少是有很多人幫上一把、有人合作、有人默許、有人甚至不敢反對,才讓一切失控至此。
死刑的邏輯是以暴制暴,然而,在轉型正義的視角下,最可以看見它的荒謬:以暴制暴的前提,必然是有一方的暴力,已經輸給了另外一方,比如死刑犯,其暴力已經先輸給了國家,於是國家才能夠好好的懲罰他們。然而,當死刑的暴力輸給了我們想它對抗的對象,又該怎麼辦?
如果今天犯錯的人,無人能動、無人敢動─比如蔣介石,比如現在正直挺挺安座高位的某些官員─我們也只能摸摸鼻子告訴自己,啊,這是天災。豈不謬哉?
死刑的意義,承平時或許難以透析,但劇變一旦發生,便顯得前所未有的無力──殺一人兩人被判死刑,但殺上一兩百萬人,你就突然之間,奪得了政權。
那麼,死刑給我們的教訓,不過就是竊鉤者誅,竊國者……侯。
正義:轉型與死刑
「說自己不清楚死刑與轉型正義的關係的人,若非太謙虛,就是太看輕死刑了吧!」
終戰至今,對於人、對於正義、對於未來,真正在思考的,不是美俄那些「贏了」的國家,而是「被放過」的那群,比如德國,比如挪威。吳豪人說,徒具形式的轉型正義,對於台灣人的正義觀傷害極深:我們總是不相信遙遠的正義,而心急於摧毀眼前的「危機」;不願意嘗試共同弭平創傷的歷程,而預先否決更生修復的可能。
但是,死刑面對我們能夠想見的、最猖獗的邪惡,卻完完全全,無可奈何……
我突然想起,訪問吳豪人老師那天,正好是鄭捷案一審判決,結果宣讀的日子。
春意希微,天氣微陰。前方還有很長的路,必須相偕而行。
* 延伸閱讀:二二八68周年談蒙古廢除死刑 (吳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