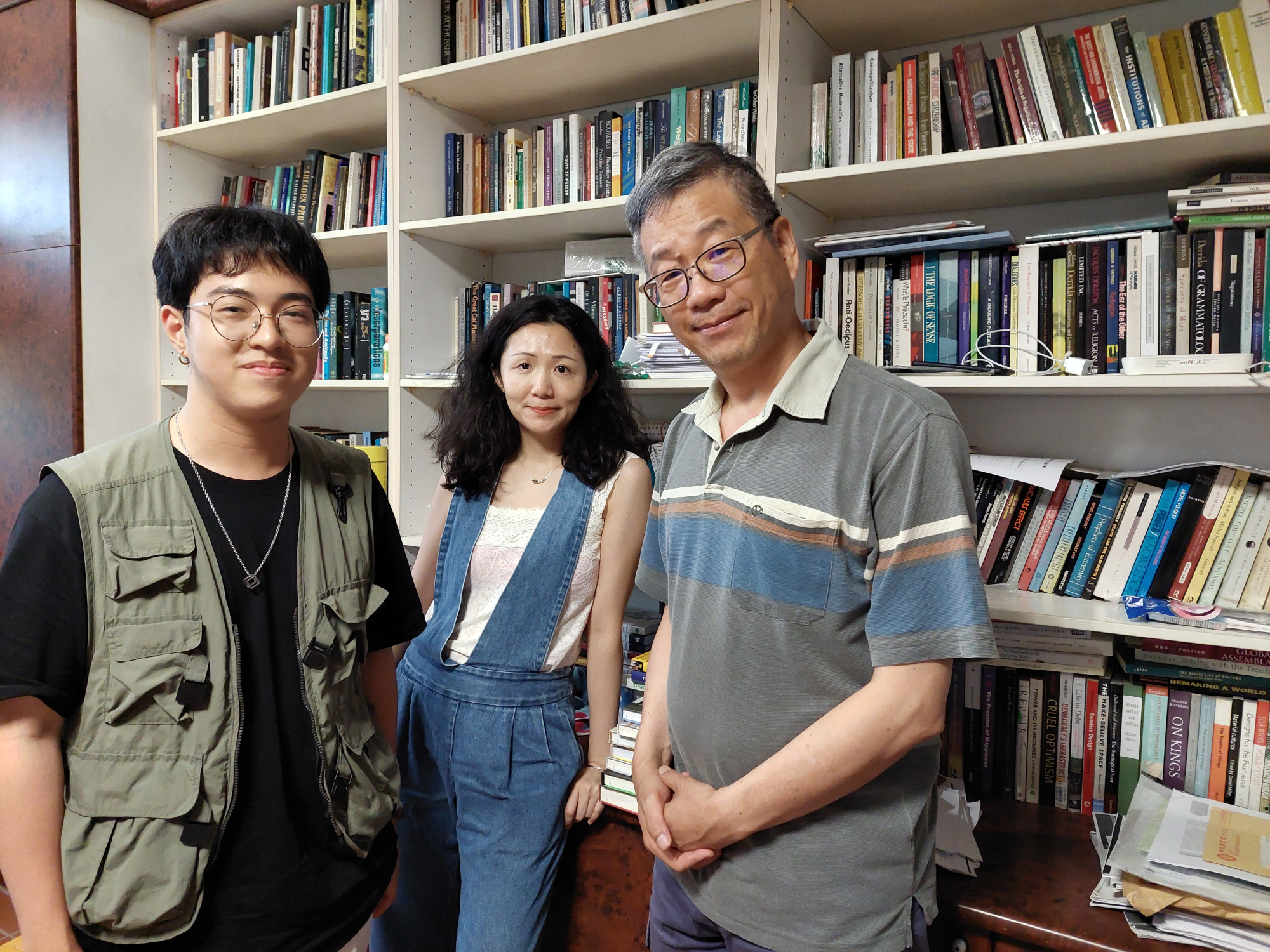電子報
廢死聯盟說的話,是為《廢話》。
在2010年的死刑爭議裡,我們受封為「最邪惡的人權團體」,我們的主張,看起來確實狗吠火車,所以《廢話》也就是「吠話」。知其不可而吠之,汪汪!《廢話電子報》於2012年2月首次發刊,每個月發行的廢話電子報是廢死聯盟實踐與社會溝通的方式之一,我們期許自己用淺白、易懂的文字,透過定期的發刊,持續跟社會對話。
一命抵一命?法律人類學與廢死運動的交集|訪容邵武
文/林楷瀚(廢死聯盟志工,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
編按:本文專訪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容邵武副研究員,容副研究員為紐約新社會科學研究院人類學系博士,曾任教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人類學碩士班,研究專長為法律人類學、政治人類學等。
「廢除死刑的理念過於『高大上』、無法『呼應台灣民情』」是我最常聽到身邊親朋好友,甚至台灣社會反對廢死的其中一個原因。
我們常想像「廢死」的法律觀念是從西方發展出來的,而台灣長期抱持著「一命還一命」的觀念,因此顯得兩種觀念格格不入、沒有交集。對當前台灣的主流民意來說,死刑具備一種正義實踐的倫理內涵,而這個平衡是不可以打破的,因此過往在廢死的推動實務上,廢死聯盟與其他倡議者的論述也難以被大眾接受。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去(2024)年4月23日憲法法庭言詞辯論時,黃丞儀研究員就指出,以台灣來說,原住民族過去並沒有死刑文化;從中國歷史來看,關於死刑的論辯也是反覆的,死刑並不是「自古以來」的傳統。如果死刑並不是某種根深蒂固的文化,我們是否有機會找尋更多與民眾溝通的可能性,以及思考台灣能否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廢死思想?
在思考這個問題的過程裡,容老師於2015年刊登在「芭樂人類學」網站的〈死刑存廢戰爭能否走出死巷?來自法律人類學的觀察〉文章引起我的注意。為了解答更多疑惑,去年七月,我與廢話電子報編輯團隊的佳臻和斯閔前往中研院民族所,拜訪容邵武副研究員。九年過去,老師對廢死運動的觀察會有何不同?
「正義」的內涵與多重轉化
容老師告訴我們,台灣長久以來無法接受廢死理念,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人們的正義觀:「犯罪之於我們的社會,就像是加害者『欠』了受害者某些東西,所以應該負起『償還債務』的責任。」但究竟要做到何種地步,才可以抵銷這種「債」呢?「極端一點地說,古代一個王公貴族被殺,可能會需要很多人陪葬;但若是一個無名之輩死了,可能也就只是死了。」在不同的文化體系與時空背景下,殺了一個人並不一定得以命相抵。
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裡有「寬恕」這樣的概念,不代表台灣沒有類似的概念,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正因為台灣與西方有著不同的歷史脈絡與社會型態,所以在考慮廢死的理念和制度如何適用到台灣時,就需要更多的思考。
「楷瀚和老師談論的這個『債』很有趣,」佳臻加入了我們的對話。她說,通常犯罪事件當中的受害者,令人同情、惋惜,毫無疑問;但因為黑幫火拼而喪命的受害者,卻不見得能得到相似的同情,這是否也是一種生命價值的落差?同時,在台灣的一些原住民族社會裡,並不認為一命抵一命才是唯一的解方,因為加害者也可能透過替被害者的家族打獵、勞動等等方式贖罪、賠償。她進一步分享,廢死聯盟2004年參加世界反死刑大會時,認識了美國的「美國謀殺案受害者家屬人權促進會」,令人驚訝的是,他們是反對死刑的犯罪被害人家屬,他們不支持死刑,也拒絕國家拿被害人做藉口,同時積極倡議犯罪被害人權益。我開始在想,我們其實已經聽過好多的案例是,被害者家屬和社會想要知道更多的「真相」,包含為什麼要痛下殺手?為什麼走到這一步?以及是否可以用死刑以外的方式,來勉強彌補被害者(家屬)的傷痛?

死刑抹煞了「可能性」
容老師接著補充,法律是一種計算生命價值的「評價體系」,在法律審判的過程裡,「一個人的命值得被如何補償、被害者家屬究竟有多痛」等問題,都是被嚴密計算並用法律機制定義的,可那背後真的可以反映一個國家的文化價值、能體現出各種不同的生命樣態嗎?
容老師回到他之前那篇文章的內容,聊起他在鄉鎮調解委員會的經歷。當車禍案件發生的時候,受害方受到的身體和其他傷害當然很嚴重,但肇事方的態度也很重要。如果肇事方在事後願意前往探視受害者、表達歉意,雙方才有可能坐下來好好談如何賠償。廢話電子報特約記者斯閔追問學理上有沒有這種討論?既然刑法限制了我們對生命的想像,為什麼沒有人去質疑?容老師解釋,這就像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典範,國家暴力成為唯一合法行使的暴力,維持了穩定性的同時,也無可避免地抹煞了異質性。
現實社會裡,有太多人對於「如何補償被害者」有著不同的聲音,很多人認為透過法律權威式地宣布「一命抵一命」就是正義的實踐,但法律體系並不能處理所有形式的傷害,因此我們需要更多的可能性。但這些可能性是不是都被「死刑」這個制度斷絕了呢?看著窗外的雷雨,我的心裡其實有點沉重。我想起林旺仁的案件,在法庭上他無論如何表示後悔,表示想和被害者家屬和解,都只被法官認定是「為了逃死而演戲」,最終仍是死刑定讞。死刑真的能讓我們看見這些可能性嗎?
廢死運動如何與社會溝通?
想到這裡,我向老師拋出一個問題:把這些關於死刑的資訊與可能性推廣給社會大眾,一直是廢死聯盟透過各種方式在做的社會對話,但往往「廢死聯盟」名字出現時,就只剩下攻擊和謾罵。
我想到德國哲學家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理論──即使他的理論也頗受批判。他重視溝通的有效性、「溝通理性」等概念;在談論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時,他也認為「討論」會從特定的資產階級開始擴大,最終推廣到整個社會。我在想,過了這麼多年,支持死刑的民意比例似乎還是居高不下,那是否意味著我們從來沒有把討論推出同溫層過?我們還有辦法做更好的溝通嗎?
「問得好,」容老師說,「就像你提到的,很多人批評他(哈伯馬斯)來自歐洲男性的觀點。並且,能夠在公共領域裡侃侃而談的,是那些受過訓練、有文化教養的人。」哈伯馬斯提供了一個理想情境,而對人類學家來說,他們會天馬行空地想像「溝通」必定是透過語言發生嗎?是不是還可以透過身體、表演等充滿創意的方式?從這個層面上看,台灣的廢死「溝通」可貴的地方在於,歐洲的政治經驗,往往是菁英立法推動廢死,看不出老百姓怎樣看待廢死;但在台灣,民間倡議者由下而上地,藉由各種方式在推動社會溝通。只用民調與時間來評斷這種溝通「有沒有效」並不公平。
這個說法讓我感到欣慰。聽廢死聯盟辦公室的夥伴說,「廢死星期四」講座在這幾年有越來越多的年輕面孔,甚至是高中生參與;我也是在高中階段,感受到公民課本和老師開始引導同學思考關於犯罪的更多可能性。
轉型正義與死刑
相較起過去只教三民主義的公民課,現在公民課堂上可以談論死刑,或多或少也代表了台灣教改的轉向。在三一八學運後,這世代的青年開始意識到國家權力的龐大,因此更加重視人權相關的議題。
容老師也認為,台灣對於死刑的研究,特別是法律人類學/法律社會學面向的研究實在太少。西方會有廢死的法律,也和歐洲曾有過納粹大屠殺的歷史背景有關。至於台灣呢?國家的性質和法律的性質,因為轉型正義工程的不完全,始終處於無法著地的情境。他非常期待,可以有更多的研究者投入這個領域,用法律人類學的視角,提供一個嶄新而突破性的觀點。
結語
訪談結束後,我們留在老師的研究室聊了很久。我轉頭看向書櫃,注意到有許多傅柯(Michelle Foucault)的著作。這位法國哲學家不僅在《規訓與懲罰》、《性史》中都談論了死刑的刑罰意義,還積極參與1970年代的法國廢死倡議。不久後的1981年,法國在前法務部長巴丹岱爾的大力推動下終於廢除死刑,如今世界上超過2/3的國家都廢死了。台灣呢?去年9月20日,憲法法庭宣判了死刑案的釋憲結果,決定了死刑像一道烏雲繼續徘徊在台灣的天空。
在我來到廢死聯盟實習的近一年裡,我常常思考廢死究竟如何用人類學的方式找到突破口,而容老師的文章和回應,又回過頭給了我答案。人類學本就擅長用邊陲、少數又有創意的觀點,向社會大眾說明社會問題的另類解方。廢死聯盟也會繼續用這樣的方式,不放棄任何溝通的可能性,也不放棄任何關於「人」的可能性。
等我們離開民族所時,烏雲已經散去,溫暖的夕陽正好。我想,不管雷雨再怎樣劇烈,只要不放棄任何希望,總會有放晴的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