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釋憲案:廢死聯盟法庭之友意見書
編按:憲法法庭開庭針對死刑違憲進行辯論。廢除死刑推動聯盟於4月9日提交我們的法庭之友意見書,本文為法庭之友意見書全文。廢死聯盟的立場絕對是認為死刑違憲。近年來的憲法解釋中,人性尊嚴的絕對保障已經是確立的憲法原則,生命權和人性尊嚴當然不可能切開來看,所以死刑必然違憲。
文/張娟芬(廢死聯盟理事長)
六條人命的負債
暌違二十五年之後,大法官終於正視死刑議題。1985年,大法官認為「毒品罪唯一死刑」合憲(釋字第194號),於是未曾奪人性命的被告黃樹明被執行死刑。1990年,大法官認為「擄人勒贖唯一死刑」合憲(釋字第263號),未曾奪人性命的馬曉濱、唐龍、王士杰被執行死刑。1999年,大法官認為「毒品罪判死刑」也合憲(釋字第476號),未曾奪人性命的王再興、周家傑被執行死刑 [註1]。
有些人支持死刑的理由是「一命償一命」。他們應該會同意,這六位未曾殺人的被告不應該判處死刑。如果台灣的違憲審查制度有一本帳冊記明大法官的功過,上面應該有這六條人命的負債。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廢死聯盟提過好幾個釋憲案,在2010年的死刑爭議中,被大法官「程序不受理」。那些釋憲案有一些是「改進死刑」的,就是指出現行死刑制度的程序保障不完備;也有一個是直接主張「廢除死刑」的。大法官在「不受理決議」中解釋為什麼不受理那些「改進死刑」的,然後假裝沒看見那個主張「廢除死刑」的 [註2]。
如此到了2024年,違憲審查制度在台灣已有超過七十年的歷史,大法官卻從來沒有針對「生命權」做出解釋。1985、1990、1999年的三次釋憲都認為沒殺人也可以判死刑,甚至可以唯一死刑,這些都是此刻的民主台灣無法想像也無法忍受之事;也就是說,過去那三號解釋已經全數過時。而2010年大法官夸夸其言,說死刑制度程序已經夠完備了,所以不受理「改進死刑」的釋憲;但這次受理死刑違憲釋憲案,題綱第二點所列舉的各項,正是那時「改進死刑」的釋憲內容。十四年以後,大法官終於遲來地承認,現行死刑制度是否完備,是具備憲政重要性的議題,值得審查。
然而十四年來,已經又槍決了三十五人。大法官的沉默,真是震耳欲聾。

自從受理死刑釋憲的消息公布之後,不,即使還沒有宣布受理之前,大眾媒體已經不斷傳出負面臆測與各種恐嚇性的說法,立委們輪流出來說應由國會決定不要由大法官決定,若廢死則賴清德崩盤,民進黨崩盤。憲法法庭在輿論壓力與憲法法理之間想必感受到拉扯,此時,限縮的合憲性解釋可能是最具誘惑性的出路:象徵性地為死刑制度加上一些條件,對人權團體有個交代,但是宣布死刑合憲,又讓大多數人安心,感覺到大法官尊重民意。如此折衷,皆大歡喜,是為「司法權的自制」。
我們不以為然。
美國聯邦憲法法院好幾次認為死刑有可能合憲,改進就好;但是好幾位大法官退休以後表示後悔在任時支持死刑合憲 [註3]。許家馨認為這是司法自制的好榜樣,表示「一個社會有機會透過自己的實踐,努力去改正自己的司法制度之後得到的反省」,「應該讓社會透過民主程序,讓人民自己來檢視,來反省。到那時候,一個社會若認為死刑制度代價太高,決定加以廢除,那個民主決定也因此取得了社會的認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數十年來給美國社會保留了這個嘗試的機會」[註4]。
死刑在台灣與在世界各國一樣,都已經有了很久很久的「實踐機會」,也都造成很多很多根本不該消逝的生命消逝了。「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記錄在案的死刑案件有八百多件 [註5],他們大多數人只不過是參加了讀書小組或者對社會改革有興趣。在非政治性的案件裡,也有超過一百六十件死刑定讞案件,罪名並不是殺人,其中有眾多的毒品案件。一直要到2003年之後,才不再有毒品案件被判死刑。這個數字還要再加上被誤判死刑並且執行的江國慶。這就是數十年來死刑制度在台灣的「實踐機會」——它是赤裸裸的國家濫權殺人,而不曾帶來「人民的反省」。拿個人的性命來讓集體的社會進行試誤實驗,在等待多數人民「反省」的期間繼續坐視個別的人類被國家奪取性命——這不正是侵害人性尊嚴的標準定義:把人類當作手段而非目的?
台灣的大法官已經以合憲解釋「自制」了三次,2010年不受理,是第四次。每一次死刑釋憲都會有人提起194、263、476三號解釋,但那六個人早已被徹底遺忘。這是死刑支持論的一貫偏誤:死刑的濫權恣意與出錯時的重大損失,從來沒有被放進等式裡去計算,好像那些死亡都免費似的。許家馨認為,「一個刑罰制度是否可以被允許,其目的審查可能是最重要的。如果目的是正當的,即便執行過程中產生有限的附隨後果,也可能是應被容許的 [註6]」。
「有限的附隨後果」。六人,三十五人,八百多人,一百六十多人,如果這是死刑機器運轉下「有限的附隨後果」,那正說明,這個刑罰不可能有正當的目的。
羅馬法、西塞羅與康德
Christopher McCrudden曾說:「人人都同意人性尊嚴是核心問題,但未必同意為什麼是、如何是 [註7]。」Human dignity,通常翻譯為人性尊嚴。這短短兩個字,值得停駐在此分析與論證,因為許多關於人性尊嚴的誤解與爭論,都源自這兩字的誤譯或者不求甚解;一旦解開,剩下的問題亦豁然開朗。
在羅馬時期,dignity [註8]是一種高階的、尊貴的「身份」。例如公職人員與政治人物對共和國有貢獻,因而得享特殊待遇,貿易公會或行會成員、專業人士或者貴族,也可能取得這個尊貴身份,所以阿岡本說dignity是一種與公共職務有關的階級(class)或社會地位(social status [註9]),哈伯瑪斯則將dignity代換為「社會榮耀(social honor)」。此時,dignity可以是複數的存在,一個人可以有多種身份 [註10];因法律與政治情況的不同,dignity可以是出生即擁有,或者後天取得;可能因為某些原因失去這種尊貴身份,也可能失而復得。取得這些身份的人可以擁有某些權力、特權、責任,或者權利 [註11],所以Teresa Iglesias說dignity是一種「差別待遇的法律手段(discriminatory legal measure [註12])」,哈伯瑪斯也點明,dignity誕生於傳統的階層化社會,而非現代的平權社會 [註13]。
這個法律概念,在羅馬共和國末期,進入了道德哲學的領域。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有鑑於凱撒大帝遇刺與羅馬的政治動盪,深感需要重建政治與公共領域的道德秩序,因此寫了《論義務》。西塞羅在書中提出human dignity一詞 [註14],他認為人類是生物中唯一能掌握理性與語言的,所以應當做出高尚的行為 [註15](例如自我節制,不向原始的肉欲屈服),實踐美德以貢獻國家社會,這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責任。
一如書名所明示,西塞羅談的human dignity不是權利,而是義務。他認為human dignity是人人皆有的,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優越天賦,既然上天給予人類這樣的天賦,那麼人類就必須負起相應的責任,所以有義務自尊自重,也有義務尊重其他人類,以及實踐其他更多的美德。雖然是為了重建政治道德,但西塞羅認為human dignity並不限於參與公共事務的社會高階人士,這是他與羅馬法的不同。但西塞羅使用了羅馬法的dignity來表達一種「身份」,以及與這種身份相應的、適當的對待關係,甚至同樣認知dignity為一種具備優越性的身份;唯一的不同只是,西塞羅比較的基準是與其他生物相比,所以所有人類都具有這樣的優越身份。
雖然「人人皆有」、「與生俱來」這樣的字眼,在後來的人權相關論述裡也頻繁出現,但是西塞羅的human dignity與後來的人性尊嚴概念,在許多意義上均大相逕庭。因為西塞羅專注於義務而非權利,human dignity只是他為人類的道德義務找到的論證依據而已——人人皆有human dignity,所以人人皆有道德義務;他用human dignity的普及性(universalization)來證成人類的絕對道德義務 [註16]。
幾乎可以說,human dignity在西塞羅眼中猶如一張借據,他可以拿著借據去向每一個人類索討:「你虧欠這個宇宙,快來盡你的道德義務!」
這就是古典時期的human dignity:每個人都是宇宙的債務人。因此哈伯瑪斯有如下的提問:古典的dignity,雖然在西塞羅手上普及化了,但是這個概念的發展系譜顯然還需要兩個步驟,才能轉變到現代的面貌。其一是:「個人的價值」這個概念是從哪裡來的?西塞羅只提出了「垂直」的人類價值——人類與其他物種相比的價值。但是「水平」的人類價值——每一個人與其他人類相比都有其價值,這個概念的出現尚有待探尋。其二是:西塞羅只提出了人類的相對價值,但「每一個人都有絕對價值」這個概念是哪裡來的?
古典與現代之間的中繼者是康德,上述兩個步驟,都可以在康德哲學中找到答案。在他的「目的王國」(kingdom of ends)裡,每個人都是目的而非手段,也必須將別人視為目的而非手段,如此便每個人都有dignity。而什麼是dignity呢?康德說:「在目的王國裡,萬事萬物若不是有個價格(price),就是有其尊嚴(dignity)。有價格的事物可以被等值的其他事物取代;而超越所有價格、沒有事物與之等值的,就有尊嚴。」如此,康德指出了「水平的人類價值」,與「絕對的人類價值」。
康德認為人因為有理性與自決,所以有人性尊嚴,此一看法,直到現在還是最具影響力的 [註17]。Oliver Sensen指出,古典時期的dignity論述有以下特質:一、dignity是一種崇高的地位,二、dignity同時具有描述性與規範性,三、dignity主要彰顯了道德責任與義務,四、從dignity推導出的倫理學是理想化的、完美主義的;這四項特質,康德的dignity論述亦全部具備,因此他承襲自古典時期的思想,並無疑問 [註18]。同時,康德肯定人本身就是目的,就有價值,大大提升了人的地位與個體性,這是他超越古典時期之處 [註19]。
人類權利與人類身份
當十八世紀人權思潮逐漸興起、民主制度在嘗試錯誤中起步,美國《獨立宣言》、美國《憲法》、法國《人權宣言》充滿了「權利(right)」的字眼,但human dignity還是靜悄悄地屬於道德哲學的範疇,在這一階段並沒有受到任何召喚。唯一例外是1849年的德國《憲法》第139條,「即使罪犯的人性尊嚴也應受尊重」,可惜這部憲法從未施行 [註20]。1911的《威瑪憲法》第151條說「每個人都應有有尊嚴的生活」,這時「尊嚴」是形容詞,dignified [註21]。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human dignity才突然接受徵召,再度進入了法律的領域,成為與「人類權利(human rights)」形影不離的概念。至此,human dignity已經在道德哲學裡被討論了兩千年。
為什麼human dignity會重出江湖呢?哈伯瑪斯認為,「人類權利」其實是一個「平等尊重所有人」的道德律令,但要落實,必須把它兌現為法律。因此人類權利就像羅馬神話裡的「兩面神」雅努斯(Janus),它有兩張臉孔,一張臉望向道德,一張臉望向法律。「人性尊嚴是一個概念的鉸鏈(conceptual hinge),將平等尊重的道德與經過民主程序立下的實證法律聯繫在一起,使這兩者得以交互作用而形成一個以人類權利為根本的政治秩序 [註22]。」
人類權利不能沒有制度性的實踐架構,這也是漢娜鄂蘭對於二十世紀極權主義肆虐的反思。漢娜鄂蘭指出,納粹的大屠殺之所以發生,正因為一方不把另一方當人看,以及執行者不把自己當作主體,而當作是系統的小螺絲釘,所以沒有責任感 [註23]。在他的分析下,human dignity正是問題的核心:納粹否定了猶太人的human dignity——人類身份,也否定了自己的human dignity——具備理性與自決的人性尊嚴。而結果就是人類權利的一場浩劫。
哈伯瑪斯說,我們總是在人類受苦的情境裡,發現既有的公民權利尚不完足,必須發明新的權利才足以除去那些羞辱與貶低,保障人類的生活。所以人性尊嚴有一種「發明」的功能,「能夠帶領我們朝向一個更為完備的既有的公民權,並且去發現與建構新的公民權。」「直覺告訴我們,人類權利從來就是因反抗暴政、壓迫與羞辱而來的產物……人性尊嚴受到侵犯的人,他們的憤怒壯大了人類權利 [註24]。」
哈伯瑪斯據此駁斥Christopher McCrudden等人性尊嚴懷疑論者。McCrudden認為人性尊嚴缺乏實質內涵,充其量只是一個佔位符(placeholder)而已 [註25]。哈伯瑪斯則說,人性尊嚴的實質內涵:「每一個人類均有平等之尊嚴」,自始即銘刻在人類權利的概念裡。二戰之後的極權主義見證,只是讓我們在震驚中意識到人性尊嚴與人類權利的密切關係;但它們自始就密切相關。
不是「佔位符」,那是什麼呢?哈伯瑪斯也想了一個比喻:人性尊嚴是民主法律秩序的測震儀(seismograph)——一種記錄震波與地震型態的儀器,有助於研究地球的內在結構。只不過人性尊嚴記錄的是「民主法律秩序的核心成份,也就是一個政治共同體裡的公民需要哪些權利,才能夠因為同為自由平等的人類、自願加入此共同體,而互相尊重 [註26]。」
奧許維茲之前與之後
自1948年的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以降,各種人權文件大量使用人性尊嚴作為核心概念。二戰確實是一個清楚的分水嶺。用Saulo Monteiro Martinho de Matos的話來說,那是「奧許維茲之後的人性尊嚴」,他所謂的「奧許維茲」並不僅僅指那個地方所發生過的歷史事件,而是用以代表那種極端侵害下的,沒有語言可以形容或訴說的人類生命型態。奧許維茲之前與之後,至少有兩個重要的差別。其一是:人性尊嚴從一種道德義務,成為一種可以主張的權利。其二是:確立了與人類身份相對應的最低待遇,也就是基本人權 [註27]。
奧許維茲之前的human dignity,雖然「人人皆有」,但與奴隸制度的存在,並不相悖。Saulo Monteiro Martinho de Matos以西元60年左右的《腓利門書》為例說明,古典用法的dignity作用僅在於辨明此人的社會角色,以及相稱的責任與待遇,並沒有為此待遇設下最低底線,所以也不介意一個人受到羞辱或貶抑 [註28]。奴役一個人並不會損及他的dignity,只要這個人確實有著奴隸的身份,那奴役他就是剛好而已;他的dignity反而是他應該認命服從當一個好奴隸的理據。
奧許維茲之後,大環境有一個重大的改變,就是眾人體認到人類權利需要制度化的保障,雅努斯面對法律的第二張臉長出來了,於是human dignity被召喚來擔任那個「概念的鉸鏈」。如何,像哈伯瑪斯說的,「將平等尊重的道德與經過民主程序立下的實證法律聯繫在一起」?
答案是,把human dignity納入正式的法律秩序。一個人有human dignity就表示他是一個權利主體,有一連串身為人類即可享有的權利,當這些權利受到不當剝奪或限制時,這個權利主體可以用法律來主張自己的權利。
奧許維茲之後的human dignity離開了康德那個理想化的「理性與自決的人」,而進入了人權法律秩序,人類權利就是他應受待遇的最低底線。Human dignity不再是義務了,它是權利;human dignity不是借據,而是債權憑證,可據以向國家索討:「快把我的權利還給我!」
如此回顧下來,human dignity的身世已經很清楚:它有至少兩種意涵,一種是康德式的理想化概念,通常以理性、自決為其特徵,譯為「人性尊嚴」可也。另一種是生而為人而有的身份與應受的對待,意思是「人類身份」。只是「人性尊嚴」的翻譯如此廣為接受,另創新譯法恐怕讀者反而不習慣,或者不知道在講human dignity,為溝通之便,只好仍然沿用「人性尊嚴」之譯。但我們必須不斷地提醒,在二戰之後的人權相關論述裡,第二種意涵才是較常出現的,而且dignity作為「身份」愈來愈受討論,也愈來愈重要 [註29];不幸地,它與「人性尊嚴」的字面意義相去甚遠,也經常造成誤解。
Saulo Monteiro Martinho de Matos清楚指出,「二十世紀,人性尊嚴為人類權利提供了基礎,它認知到每一個人類都具備權利主體的地位 [註30]」。這種主張立刻讓我們想起第一個以釋憲方式廢除死刑的匈牙利憲法法院院長拉斯洛‧索游(László Sólyom)。在1990年宣布死刑違憲的意見書裡,索游從《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人類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說起,他認為人性尊嚴的平等可以推導出平等權:「平等尊嚴的權利與生命權結合在一起,就是要確保法律之前,即使被視為具有不同『價值』的裸命(bare lives)也不會受到差別對待。每個人擁有生命的權利都是一樣的。一個跛腳的人和一個道德上有罪的人,他們的生命權與人性尊嚴同樣不可侵犯,因為尊嚴是平等的。人性尊嚴,人皆有之,無論他因為何種原因、取得了多麼大的成就。」索游同樣把人性尊嚴代換成法律地位的平等。
將human dignity解作「人類身份」,我們亦可以了解索游的另一重要主張:生命權與human dignity不可分割。具體的肉身和抽象的「人類身份」怎麼可能分開?如果沒有肉身即失去人類身份,亦不可能空有人類的肉身而不具人類身份。如果要取消一個人的人類身份,唯有殺死他的肉身一途。德國科隆大學教授Thomas Weigend出具的專家意見也指出,「人唯有在保有生命的情況下方得以享有人性尊嚴,亦即,剝奪一個人的性命將同時摧毀其人性尊嚴的根本」(如附件一、二)。
關於生命權與人性尊嚴,我在2015年模擬憲法法庭的協同意見書(如附件三)已經詳述,這裡不再重複。但是這次從頭釐清human dignity的演變歷史之後,我必須提出一個重要的修正。在模憲意見書裡,我與多數論者一樣,在大法官既有的憲法解釋裡找出那些以人性尊嚴為基礎的權利,例如自決、隱私權、人格權、思想自由等等,把它們當作人性尊嚴的內容。我寫道:「生命權是全有或全無的,因為生死殊途。侵害生命權就是使那個人死掉、全部死掉、並且永遠死掉,沒有『死去一點點』的可能,沒有『死掉這一部份,但是另外一部份繼續活著』的可能,也沒有『死去一段時間,過一陣子再復活』的可能。生命權的損害是全面的,永久的,這是生命權所獨有的特性。人性尊嚴就不是這樣,例如一個人的隱私被侵犯,人性尊嚴部分受損;或者一個人被販為奴隸時自決能力盡失,可是人口販運組織被破獲以後,奴隸就恢復了他之所以為人的品質。人性尊嚴(或任何其他基本權)的損害有可能是部分的,也有可能回復。」
當時我主張生命權與人性尊嚴並不是一個整體。如今我對人性尊嚴有了新的理解:那些權利不是人性尊嚴的內容,而是從人性尊嚴推導而出;那些權利是人性尊嚴生出來的小孩。人性尊嚴正確的解法就是「人類身份」。
一旦解為「人類身份」,一切就豁然開朗:是的,人類身份也是全有或全無的,也是一旦失去就不可回復的,也是其他權利的基礎,失去人類身份即失去所有其他的權利;因此,索游的主張是對的,生命與人類身份是不可能分割的,它們是一個整體。
艾希莫夫有一部科幻小說《雙百人》,講一個機器人想要變成真正的人。故事寫得很法律,機器人精心佈局以後,上法庭打官司爭取「人籍」——他要被正式承認為人,要取得人類的法律地位。「人籍」的用語翻得極好,與「戶籍」「國籍」同樣的概念。「人類身份」也就是「人籍」的意思。
肉身死亡即失去戶籍與國籍,當然也會失去人籍。失去生命,必然失去人籍,失去人類的身份。有人說人死了還可以有尊嚴,那是被「人性尊嚴」這個字面的意義給誤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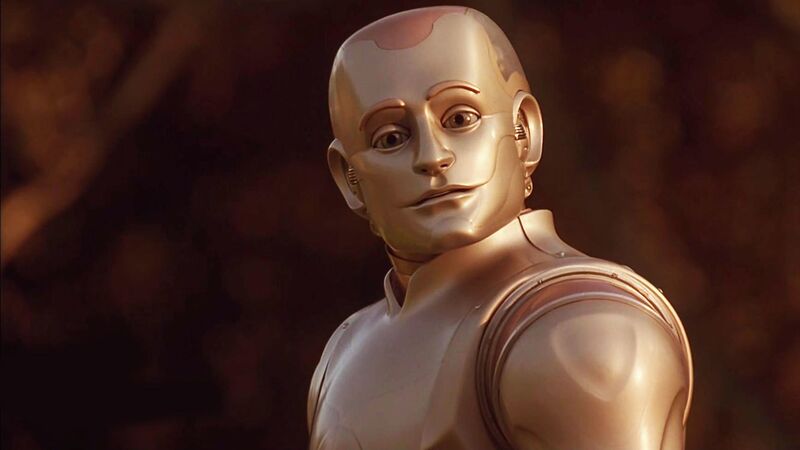
國家不能處置生命
生命權與人性尊嚴的同一性,是支持死刑的論者所不能接受的,因為在台灣,人性尊嚴的絕對保障是已經確立的憲法原則,如果不能將生命權和人性尊嚴切開來,就必然會得出死刑違憲的結論。許家馨以戰爭與正當防衛為例,企圖論證生命權與人性尊嚴可以分割,他的論證大致如下:(1)戰爭時,國家以武力殺敵,那就侵害了敵軍的生命權。(2)正當防衛時,國家雖未動手,但殺人的行為被國家評價為阻卻違法,因而不加非難或懲罰。此二例均可說明,在承認人性尊嚴需絕對保障的前提下,某些狀況仍可奪取生命,可見生命權與人性尊嚴可以分割,不是同一體 [註31]。
許家馨認為,正當防衛之阻卻違法,「牽涉到對於生命價值的判斷」,並引用南非憲法法院的死刑判決做為佐證。南非憲法法院死刑判決裡有這一段話:「正當防衛是所有法律系統都肯定的概念。如果要在兩個或多個生命之間作選擇,那麼無辜者的生命,將會優先於攻擊者」,許家馨認為,這表示國家可以評價人民的生命價值高低。
正當防衛的要件是:不法之侵害、侵害的現在性、目的是防衛、最後一個防衛時點、手段沒有過當;這是普遍接受的法理。南非憲法判決裡的那段話被理解為「對生命價值的判斷」,顯然有誤,因為那段話裡的「攻擊者」、「無辜者」、「犯罪者」、「受害者」,不是針對任何一方的人格評價,而純然是依照刑法的法理,判斷在該緊急事件裡,誰是不法行為的行為人。如果蝙蝠俠綁架了小丑並且動用足以致死的私刑,則小丑就是上述引文裡的「無辜者」,蝙蝠俠是「犯罪者」。如果小丑伺機反擊而殺害蝙蝠俠,小丑即適用正當防衛,他殺害蝙蝠俠的行為不會受到法律的責難。即使我們都知道小丑作惡多端而蝙蝠俠行俠仗義,但蝙蝠俠就是上述事件裡的攻擊者,小丑就是受害者;這跟蝙蝠俠與小丑誰的生命比較有價值沒有關係,國家的法律尤其不可以去評價他們兩人誰的生命價值比較高。
許家馨另引用匈牙利憲法法院判決來討論正當防衛:「在協同意見書裡,大法官Sólyom 指出正當防衛會對如此的論理造成難題。他認為如果生命價值先於經驗,政府根本無權剝奪人命,則正當防衛也無從正當化。政府並無權利剝奪被告的生命,也無權要求被害人忍受可能使其失去生命的攻擊 [註32]。」從索游的意見書看來,我倒不認為他有感到什麼難題,事實上,索游完整的分析了正當防衛為什麼是阻卻違法:「當受害者殺死其攻擊者時,法律基於『正當防衛』而不懲罰這個殺人行為,並不是因為法律承認這個剝奪生命的行為合法,而是認為這個攻擊與反擊,超出了法律所能及的範圍。正當防衛只發生於必須在幾個生命之間作選擇的時候,這是『死亡的重新分配(redistribution of death)』,唯有犧牲攻擊者的生命,受害者才能存活。然而法律不應區分或重新分配死亡。在這種情況下,法律既不要求受害者負責,也不賦予受害者權利。法律既不能授予被害者殺死攻擊者的權利,也不能要求受害者承受此行為,因為這已涉及處置其生命的權力。於是,必須在幾個生命之間作選擇的那些時刻,人類回歸到自然狀態。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解釋亦復如是:求生本能可以突破所有文明的障礙——也就是不限人類才能擁有的生存權(「動物也能擁有」的權利)。當這種面臨選擇的情境終止時,法律才再度介入,但它只在職權界線內檢視——也就是,是否存在『正當防衛的情況』,但不對當時的事件進行評價 [註33]。」
「法律基於『正當防衛』而不懲罰這個殺人行為,並不是因為法律承認這個剝奪生命的行為合法,而是認為這個攻擊與反擊,超出了法律所能及的範圍。」這是關鍵——並不是因為法律承認這個剝奪生命的行為合法。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說,是因為不法侵害的現在性,使得法律不能以平常的標準去要求受害者,事件的緊急程度損害了受害者的責任能力,導致法律不可加以課責。
除了索游的解法以外,還可以提出更多的論證。許玉秀指出,戰爭或正當防衛時如果做出致人於死的行為,不應稱為殺人,因為那是防止法益受害的行為。「他們的行為如果造成死亡結果,必須被檢驗是不是符合保護法益的必要和不得已,致人於死僅只可以是保護法益行為的附隨結果,不可以是直接故意的對象」。如果造成死亡,那是未必故意或有認識過失 [註34]。確實,正當防衛的要件裡,已經指明了「目的是防衛」,因此構成正當防衛的行為,必然不符合殺人的構成要件。
綜合以上的分析,結論是:「戰爭與正當防衛就可以殺人,可見生命權保障有例外/生命權是相對保障/生命權與人性尊嚴可以切開」這個主張是錯誤的,因為那不構成殺人,不懲罰防衛者的原因是國家不可介入生命的處置,這也是為什麼不可以有死刑的原因。「正當防衛」與「國家保護生命權」兩件事並不牴觸,它們背後的共同原則,就是國家不可妄自評斷人民的生命價值,不可介入處置人民的生命。
集中營的牆
二戰時期,奧許維茲集中營的指揮官魯道夫‧霍斯,就住在集中營旁邊。一牆之隔,高階納粹軍官家庭美滿,居室整潔,花園由太太設計維護,孩子們健康活潑地在戶外跑來跑去,天際線常常是一縷煙。官太太們自然地談起從哪個猶太人那裡拿到一顆鑽戒或一襲長裙,「他們好會藏,好狡猾!」官員們則拿出藍圖來討論,怎樣的設計可以讓焚化爐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悶燒。
這是電影《夢想集中營》,甜美生活的背景裡,偶爾有慘叫,骸骨,屍煙,而在此生活的這些人毫不介意。指揮官太太的母親來訪,看到戰爭中還有這等排場,非常欣慰:「女兒,你真的做到了!」指揮官太太毫不謙虛地笑。他快樂極了。
母親參觀美麗的花園,一抬眼,有些愕然,問道:「那是集中營的牆嗎?」
女兒想也不想就回答:「對,我們正在種藤蔓,等到長好就看不見了。」
不需等藤蔓長好,他們已經過著夢想的生活,隔牆之事再如何明顯,他們都可以保持不知道,沒看見。當一個人類對於另一個人類所受的待遇毫無所覺毫無所感,那就是失去human-ness的時刻,就像殺羊時不必避忌別的羊在場,因為羊們不過睜著那冷淡的小眼睛不發一語罷了。
支持死刑的義憤有一部分是這個東西,像勒瑰恩寫的那個折磨無辜的孩子而達成繁榮的城市,甜美幸福的生活只需要犧牲一個孩子 [註35]。才一個。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何樂而不為。為了心安理得的活下去,市民會說服自己,那個犧牲的一定不是孩子,是罪人。然後無邊無際地想像他的罪,已經犯的與還沒犯的,有證據的與沒證據的;如果他今生無罪,前世一定是惡人,不然就是來生!也許是極端之惡……。
如果大法官做出合憲性解釋,留著殺人機器但為它添加裝飾性的綠意生機,那就是在圍牆上面種藤蔓。
從我寫〈殺戮的艱難〉[註36] 至今,二十年了。參與廢死運動的過程中,真正令我無法直視的殘酷,往往是這個簡單而悲哀的事實:人們也只是睜著冷淡的小眼睛不發一語。偶爾,我覺得很難壓抑內心的荒謬,我們竟然在辯論「我可不可以殺死他但是沒有傷害他的人性尊嚴?」
只要還有死刑,我們就是住在集中營外面而成天小確幸的那一家人。
有人說:「領導管絃樂隊時,你必須背對群眾。」謹以此堅定的智慧,寄語大法官。

圖/by SteFou! on Flickr
註解
[1] 釋字476號解釋是當時台北地方法院法官陳志祥暫停審判後聲請解釋,原因案件有兩件,可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獲得合憲解釋之後,這兩件共五名被告並未被判處死刑。但適用同一法條的另一販毒案件,有兩名被告被判死刑並執行。
[2] 2010年的死刑釋憲,詳見張娟芬,〈廢死釋憲的折返跑〉,《殺戮的艱難》,行人出版社,頁186-222。
[3] 劉靜怡,2015,協同意見書,《放棄死刑走向文明》,頁146-147。
[4] 許家馨,2015,部分不同部分協同意見書,《放棄死刑走向文明》,頁183-184。
[5] 謝孟達,2012,《生死之間:戒嚴時期政治案件死刑判決之研究》,政大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6] 同註4,頁211。
[7] Christopher McCrudden, Human Dignity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Human Right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ume 19, Issue 4, September 2008, Pages 655–724, https://doi.org/10.1093/ejil/chn043
[8] 拉丁文原文是dignitas,為免蕪雜且方便理解,以下均以dignity表示。
[9] de Matos, S.M.M. (2022), "Human Dignity after Auschwitz: Some Animating Ideas", Sarat, A., Pele, A. and Riley, S. (Ed.) Human Dignity (Studies in Law,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88),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 Leeds, pp. 83-97. https://doi.org/10.1108/S1059-433720220000088005
[10] HABERMAS, J. (2010). THE CONCEPT OF HUMAN DIGNITY AND THE REALISTIC UTOPIA OF HUMAN RIGHTS. Metaphilosophy, 41(4), 464–480. http://www.jstor.org/stable/24439631
[11] 同註9。
[12] Iglesias Teresa, 2001. ‘‘Bedrock Truths and the Dignity of the Individual’’, Logos: A Journal of Catholic Thought and Culture, vol. 4, pp. 111-34.
[13] 同註10。
[14] 拉丁文原文是dignitas humana,為免蕪雜且方便理解,以下均以human dignity表示。
[15] 原文是honestum,蕭高彥譯為「高尚性」,見〈西塞羅與馬基維利論政治道德〉,《政治科學論叢》,頁1-28。
[16] 同註9。
[17] 同註9。
[18] Sensen, Oliver (2011). Kant on Human Dignity. De Gruyter. (2011, p. 164)
[19] Paolo Becchi, Klaus Mathis, (2019). Handbook of Human Dignity in Europe. DOI: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28082-0.
[20] 同註10。
[21] 同註10。
[22] 同註10。
[23] 漢娜鄂蘭,2013,《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玉山社出版。
[24] 同註10。
[25] 同註7。
[26] 同註10,斜體字為原文。
[27] 同註9。
[28] 同註9。
[29] 例如Saulo Monteiro Martinho de Matos,同註9; John Bessler, The Death Penalty's Denial of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Paolo Becchi, Human Dignity in Europe: Introduction, Handbook of Human Dignity in Europe; Jeremy Waldron, Dignity and Rank: In memory of Gregory Vlastos (1907–1991).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8(2), 201–237. doi:10.1017/S0003975607000343等等。
[30] 同註9。
[31] 許家馨,部分不同部分協同意見書,《放棄死刑走向文明》,頁175-211。
[32] 許家馨,2021,〈跨國憲法對話中的生命權與死刑〉,《東吳公法論叢》第13卷,頁45-88。
[33] 匈牙利憲法法院的死刑違憲判決全文翻譯,可參考《死刑釋憲三國志》(書名暫訂),即將出版。
[34] 許玉秀,〈死刑違憲論述補遺(代序)〉,《放棄死刑走向文明》,頁7-14。
[35] 勒瑰恩獲得雨果獎的小說,〈離開歐梅拉斯的人〉:「所有的歐梅拉斯人都知道他在那兒……他們都明白他必須待在那兒…所有人都清楚一個道理:他們的幸福生活,他們的城市美景,他們之間親愛和睦的關係,他們孩子的健康……甚至連他們天地裡的風調雨順、五穀豐收,一切全有賴那孩子受苦受難……如果將孩子弄出那個悲慘地方,讓他重見天日,幫他洗澡,把他餵飽,給他舒適,當然是好事一件。但只要那麼做了,歐梅拉斯的一切繁榮景象、美麗景色、歡樂生活都會頃刻化為烏有。」
[36] 〈殺戮的艱難〉一文最初發表在《司改雜誌》,是2004年。
附件1 Thomas Weigend. April, 2024. Germany, A Country without Death Penalty. Expert Opinion. The German Federal Bar (BRAK). 1~19
附件2 Thomas Weigend,2024年4月,〈德國,一個沒有死刑的國家〉專家意見書,德國聯邦律師公會。(即上開附件1之中文翻譯) 20~35
附件3 張娟芬,〈(模擬憲法法庭)大法官張娟芬提出協同意見書〉,收於:台北律師公會主編《放棄死刑走向文明》乙書,頁113-133,2015年9月。 36~56
| 附加檔案 | 大小 |
|---|---|
| 707.58 KB | |
| 1.19 MB | |
| 1.87 MB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