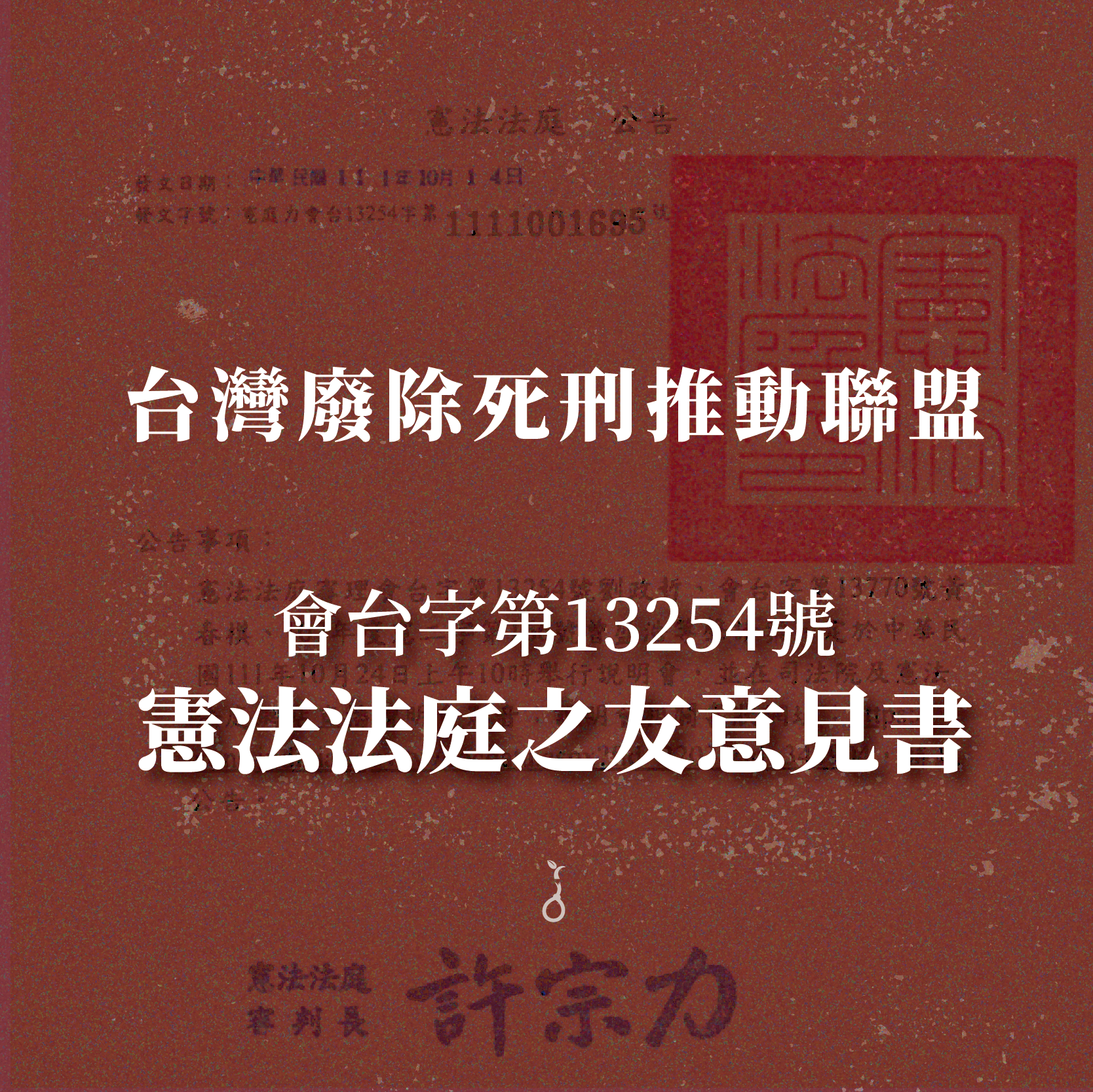倡議與行動
這裡會有廢死聯盟的新聞稿及倡議行動。
會台字第13254號憲法法庭之友意見書
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會台字第13254號憲法法庭之友意見書(PDF檔下載)
主案案號:會台字第13254號
法庭之友: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代 理 人:張娟芬(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理事長)
代 理 人:李念祖(東吳大學法研所兼任教授)
*本意見書之提出,與當事人、關係人及其代理人沒有分工合作關係,也沒有收受他們的金錢或物質報酬,特此說明。
法官迴避,是為了讓一般人感覺到「法院看起來是公正的」。法官迴避原則並非出於對於法官的能力與品格抱持懷疑,而是為了更高的目的:為司法權爭取民主正當性。司法權是民主制度中不以多數民意為基礎的權力,亦不定期汰換改選;因此,它必須積極地取得民眾信任。
這裡的關鍵詞是「一般人」與「看起來」。耶魯大學教授Tom Tyler的研究顯示,「一般人」是否接受法院的判決、是否服從法院的權威,取決於法院在程序上是否公平(fair),Tyler稱之為「程序正義效應」(procedural justice effect)[1]。自八〇年代累積至今,關於「程序正義效應」的研究已經汗牛充棟,結果都顯示,當人們感受到法院採取公平程序時,便比較願意服從判決結果,而且這時人們對於判決結果的評價也比較高[2]。換句話說,法院必須在程序上顯得公平無偏,方能取得民眾信任。
台灣的死刑冤案救援行動,自蘇建和案以來,已經將近三十年。救援行動經常受到民眾的質疑:「不是三級三審嗎,而且這些案子不是都已經發回更審好多次了嗎?」「四、五十個法官都判他們有罪,難道四、五十個法官都錯了嗎?」在一般人眼中,審級制度就是不斷糾正錯誤的程序,每一審都不斷有新的法官加入;因此當案件定讞,他們便相信這是集結了眾多法官,反覆調查思考之後的結果,不會錯。在一般人看來,這樣的法院在程序上是公平的。
不幸的是,此次提出釋憲的死刑案件正是對於民眾信心的一大打擊。與一般人想像的不同,死刑案件中法官重複的情形非常嚴重。在高等法院的重複共有十一案,例如李德榮案,蔡長林法官審他的更一、更三、更六,葉居正法官審他的更二、更五、更十,黃崑宗法官審他的更三、更六、更八,董武全法官審他的二審、更七,田平安法官審他的更一、更三,吳森豐法官審他的更五、更九;沈鴻霖案,羅得村與劉榮服法官審他的二審與更四,陳紀剛、姚勳昌法官審他的更二與更五,江德千法官審他的更三與更七;陳文魁案,葉居正法官審他的二審、更二、更四,董武全法官審他的更一、更六;劉榮三案,袁從禎、姚勳昌、郭同奇三位法官審他的更一與更三,李文雄法官審他的更二與更五;郭俊偉與謝志宏案,葉居正法官審他們的更一與更三,陳義仲、蔡勝雄法官審他們的更四與更七。
在最高法院的重複共有三十六案,這就不必列舉了,因為最高法院有「重大案件連身」的規定,死刑、無期徒刑案件只要上到最高法院,就不再抽籤分案,直接劃歸同一組法官重複審理[3]。至於非重大案件則從更二審以後開始連身,稱為「更二連身條款」。
「連身條款」是最高法院的分案內規,自一九八七年開始,系統性、大規模地製造法官重複的情形。而高等法院的法官重複情形亦不遑多讓,可謂交叉持股,錯綜複雜。一般人對法院判決的信任基礎,就這樣被實務作法淘空了地基。
案件由同一法官反覆審理,容易引起民眾的不信任,原因非常簡單:要求法官改變立場「自證己錯」,違反人性。
卡夫卡在《審判》裡寫過這樣的故事。一個鄉下人來到法院,但守門人不讓他進去。鄉下人問,何時可以進去呢?守門人不置可否。法院的大門是敞開的,鄉下人從門口望進去,好像想要蠢動的樣子。守門人從容微笑說:「我要提醒你,我是有權力的。裡面每個大廳都有守門人,一個比一個更有權力,而我是這裡級別最低的。那第三個守門人啊,呵,連我也不敢看他一眼啊!」於是鄉下人想,還是必須得到允許以後才能進去。守門人給了他一張凳子坐,鄉下人日復一日地懇求,守門人總是冷淡地說,現在還不行。鄉下人每天盯著守門人,已經無法可想。他試過賄賂,守門人收了以後說:「我收下只是避免你誤會,以為你有什麼該做的事情沒有做。」日升月落,鄉下人連守門人衣領上的跳蚤都熟識了,他哀求跳蚤替他說服守門人改變主意。最後鄉下人垂垂老矣,將死之際,心裡還記掛著多年來的疑問。他問守門人:「這麼多年來,為什麼從來沒有別人要進法院呢?」守門人體諒鄉下人已經耳背,便彎下腰來在他耳邊吼道:「因為這道門就是專門為你而設的!現在我要去把它關上了。」
當人民來到法律面前,一再看見同樣的臉孔拒絕他,他就不會再相信法律的莊嚴。他會絕望地認為,法院只是一齣荒謬劇,而他是劇中被愚弄的鄉下人。
法官也會犯錯,是實證研究的一致發現。Chris Guthrie曾經以167位美國聯邦司法官(federal magistrate judge)為對象,測試他們的認知錯覺(cognitive illusion),發現法官也難以擺脫五種常見的認知錯覺,其中「錨定效應」(anchor effect)、「後見偏誤」(hindsight bias)、「自我中心偏誤」(egocentric bias)三項,數據顯示法官與素人的偏誤風險程度並無差別[4]。這是因為我們做決定時,必然借用經驗法則(heuristics,或譯「捷思法」)來加速決斷過程,這樣的思考捷徑大多數時候很管用,但有時候會帶來一些不精確的推論,最終導致判決的錯誤[5]。其中,加拿大學者Emma Cunliffe的研究尤其值得注意,因為美國的刑事訴訟制度多半由陪審團來認定事實,法官的角色與功能與台灣差異很大,幾乎無法類比;但加拿大百分之九十九的刑案都是法官審判而沒有陪審團,因此加拿大的法官和台灣法官一樣,負責根據證據來認定事實,並且必須完整交代論理的過程。不意外地,Cunliffe的研究也顯示職業法官無法倖免於各式認知偏誤[6]。更糟的是,諸多認知偏誤之上還有一種「偏誤盲點」(bias blind spot),就是低估自己的偏誤、高估別人的偏誤[7];聰明人也無法避免偏誤盲點,甚至因為自恃聰明、認為自己可以倖免,而陷得愈深[8]。
認知錯覺多半不是故意的,為數眾多的心理學研究在醫生、會計師、律師、房屋估價師、工程師等各種人身上發現認知錯覺,法官只是各行各業中的一種。就像美國法學家Jerome Frank說的,「到頭來我們只能面對這個事實:法官也是人。」
當法官審理一個他已經審過的案件,他的心理機轉除了以上通則之外,又增加一層「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Leon Festinger的認知失調理論指出,我們有一個以上的選項而且很難選時,做了選擇以後會懷疑自己選得對不對,如果選錯了,會覺得自己像笨蛋。認知失調幾乎是做決定之後必然隨之而來的情緒,而克服這種不快的情緒,是人的本能之一。決定愈困難,隨之而來的認知失調愈大,去降低認知失調的動機就愈強烈。認知失調對於法官的影響方向未必能夠預測,但重點是他的決策會受到個人心理動機的影響,而非如司法制度所期待他的,純粹考量法律因素來下決定[9]。
法官也是人,他做的決定影響別人的生命至鉅,但認知錯覺卻無法避免,怎麼辦?答案亦十分簡單:讓多元觀點進入決策過程[10]。繞了一圈,其實就是回頭恪遵司法制度設計的本意:讓其他的法官來看看。不同的法官,不同的心理機轉,或許就有互相牽制激盪的機會。
有一個瑞典實驗非常精彩地呈現了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及其應對策略[11]。「確認偏誤」指的是做決策時無意識地挑選合乎原先看法的資訊,而忽略或輕視矛盾的訊息,一意孤行,終於形成隧道視野。這實驗有兩組受試者,一組是64位瑞典法官,一組是80位法學院學生。實驗者想知道羈押的決定會不會觸發有罪的決定,所以他讓每個受試者判八個案子,其中四個讓他自己決定要不要羈押,另外四個由別人決定要不要羈押。結果是:如果這被告是受試者自己決定要羈押的,後續審判時就比較傾向於判有罪,如果是被別人羈押的則不會;也就是說,同一人先決定羈押再決定論罪,就會出現確認偏誤。
實驗者還想知道,如果我們減輕受試者的認知負擔,能不能減低確認偏誤?所以他請一半的法學院學生直接讀完卷證綜合判斷,另一半逐一判斷每一證據的強度;結果是:這一項對於判有罪還是無罪沒有顯著影響。綜合起來,這個研究的結論是:要對抗確認偏誤,改變證據評價模式的效果非常有限,真正有用的辦法,就是換一個人,截斷那個從確認偏誤到隧道視野的流程。
不得不懷疑:只是決定羈押就足以觸發確認偏誤,那麼曾經判過有罪難道不會觸發確認偏誤?
如同多位學者在諮詢意見中指出,司法系統預設法官是無所偏私的(presumption of impartiality),因此美、德、日、歐洲人權法院,都有這麼一句話:「僅僅法官重複,不能推定為偏頗。」但是這句話應該是論證的起點,而不是終點。「法官重複」加上什麼因素,會得到「可能偏頗,必須迴避」的結果?
歐洲人權法院2021年的孟小姐案[12]可以用來回答這個問題。德國的孟小姐有個丈夫,兩人已經分居;她另外交了男朋友。丈夫開始把資產慢慢地移到海外,這將使得孟小姐無法分到財產,男友也無法透過孟小姐分享這些資產,於是男友將丈夫殺了,動機是貪婪。檢察官以謀殺罪起訴男友,要傳孟小姐出庭的時候,他們兩人已經訂婚了,孟小姐拒絕證言,但男友還是被判有罪,無期徒刑定讞。
男友的官司結束以後,檢察官起訴孟小姐,並且找男友出庭作證。男友很沒有道義的翻供,說孟小姐深恨其夫,買兇殺人。孟小姐也被判無期徒刑。
所以這是同一殺人案的兩位共同被告,分別在兩個獨立程序裡受審。這兩個程序裡有一位法官M是重複的。孟小姐在審理過程中便一直主張法官M要迴避,不過區域法院考慮過後認為不用迴避。等到案件定讞以後,孟小姐便到歐洲人權法院來,告德國政府。孟小姐主張,M法官在男友判決裡已經認定了孟小姐和男友一起策劃謀殺丈夫,表示M法官審判孟小姐時已經有預斷,那就違反了歐洲人權公約第六條:審判必須由獨立而公正的法庭為之。如果法官心中已經未審先判,那當然不是公平法院。
歐洲人權法院過去有過類似的案子:分別審理共同被告時,法官未迴避。那幾個案子,歐洲人權法院都判決「無理由懷疑法官偏頗」,主要考慮了三個因素。第一,前行審判有「認定」後續審判的被告犯罪嗎?比如說有沒有犯行的細節描述,或者包含了犯罪構成要件?例如Schwarzenberger案,法院判決並沒有認定Schwarzenberger犯案,而純粹是引用同案被告的證述;又如Poppe案,法院判決只是提到Poppe的名字而已,沒有認定他的犯行;又如Miminoshvili案,被告名字從未被提及;又如Ferrantelli and Santangelo案,對被告的指控是目擊證人所言,不是法院的認定[13]。這些情況下,歐洲人權法院均不認為被告[14]有理由懷疑法官偏頗。
反過來說,如果「法官重複」+「前行判決已經給予法律評價」,那歐洲人權法院就會認為被告懷疑法官不公正是有理由的,政府會敗訴。
第二,後續審判有沒有實質調查?後續審判在多大程度上依賴前行審判?如果沒有調查,後續審判大幅使用前行審判的調查結果,「法官重複」+「後續審判被架空」,那歐洲人權法院便可能認為被告有理,政府敗訴。(孟小姐案的審判有實質調查,而且判決沒有沿用前行判決。)
第三,這個重複的法官是職業法官還是素人法官?歐洲人權法院認為職業法官較有能力將前後兩案分別開來考慮,因此如果「法官重複」+「素人法官」,歐洲人權法院便可能認為被告有理,政府敗訴。(孟小姐案重複的這位M法官是職業法官。)
與前例不同,孟小姐勝訴了。她贏在第一個考量因素:M法官在男友判決裡明確認定孟小姐與男友共同決定殺夫並擬定謀殺計畫。例如丈夫死訊傳出時,孟小姐與男友都沒有問死因,前行判決認為這是「他們」犯案或涉案的跡象,「他們」就是指男友與孟小姐;可見前行判決已經完全把孟小姐當作共犯。
歐洲人權法院並不是認定法官M有偏頗、預斷,所以判決孟小姐勝訴;而是認定孟小姐懷疑法官M有預斷是合理的,孟小姐就勝訴了。這一點值得慎重地強調:關於「法官迴避」議題,不需證明法官確實有預斷,只需證明「被告的懷疑是合理的」,便足以判被告勝訴。
同樣值得慎重強調的是:對歐洲人權法院來說,「法官重複」+「前行判決認定被告罪行」,就違反了歐洲人權公約的「公平法院原則」。無論法官事實上有沒有預斷。
第三點值得慎重強調的是:歐洲人權法院把「法官無偏頗假定」當作論證的起點,而不是終點。它具體考量了三個相關的因素,以釐清被告的懷疑是不是合理。
那麼,本次釋憲的死刑案件,「具體情況」如何?台灣法界主流意見,至目前為止,都延續釋字一七八號解釋的論點:法官不可審查自己的判決,但是二審重複就沒關係,因為先前的判決已被最高法院撤銷,不復存在,所以同樣的法官第二次審理時,並不是在審查他自己的判決。本次釋憲的專家與相關機關都持相同意見。
廢死聯盟針對二審法官重複的十一案,就判決進行比對[15],結果如下表。
*法官重複審次之判決比對結果:
| 聲請人(及比對之判決) | 事實欄重複比例 | 理由欄重複比例 | 整體重複比例 |
| 施智元(二審vs更三) | 62.0% | 64.0% | 63.6% |
| 陳文魁(二審vs更二) | 59.8% | 64.6 % | 63.5% |
| 沈鴻霖(更二vs更五) | 82.3% | 54.5% | 59.4% |
|
蕭仁俊、廖家麟(更四vs更八) |
66.5% | 44.1% | 45.5% |
| 郭俊偉、謝志宏(更四vs更七) | 67.7% | 58.6% | 59.5% |
| 李德榮(更三vs更六) | 76.3% | 53.7% | 57.2% |
| 劉榮三(更一vs更三) | 65.9% | 48.8% | 51.1% |
| 陳錫卿(更五vs更八) | 85.2% | 67.8% | 69.9% |
| 鄭性澤(二審vs更二) | 94.7% | 80.5% | 81.7% |
| 平均 | 70.7% | 57.0% | 58.7% |
數字說話了:十一個死刑案件不是法官重複「而已」;是「法官重複」+「嚴重依賴前行判決」。鄭性澤的案件事實欄有94.7%重複,理由欄有80.5%重複,整體重複比例81.7%。意外嗎?不必意外,因為鄭性澤的二審法官是洪耀宗、江德千、劉登俊,更二審法官仍然是洪耀宗、劉登俊、江德千,原班人馬,只是受命與陪席互換而已。
看著這樣的統計結果,我們是否還能說,「當更二審開庭的時候,原來的二審判決早就被廢棄了,所以洪耀宗、劉登俊、江德千並不是在審查他們自己的判決,不會有預斷」?他們就是在審查自己的判決!
台灣的司法判決實務顯示,高等法院的判決即使被最高法院撤銷發回,也不會消失,而會被包裹進後來的判決裡,借屍還魂。釋字一七八號解釋已經明示,如果一審法官後來在三審的時候審查自己的判決也必須迴避,因為他會間接審查到自己的判決;那麼二審重複的情形又豈可容忍?
已經平反的前死刑犯人謝志宏說得很好:「原判決撤銷,但有一個東西是沒有撤銷的,就是自由心證。」同屬過來人的鄭性澤則淡淡地說:「更審嗎?一指神功而已。」
認知錯覺、認知失調等心理機轉,不會因為判決形式上被撤銷了就不存在。當更三審的法官收到一個他在更一審已經判過的案件,他不會視之為更一審的延長賽嗎?他不會把握這個機會繼續補充資料,爭取上級審的認同嗎?
思考法官迴避的問題本不應該以判決為單位,而應該以案件為單位。曾經把鄭性澤判死刑的法官,後來知道他成功平反,內心可能依然頑固地認定一定就是他,也可能自我安慰說是以前科學鑑定技術有限,所以不能怪法官;無論何者,裡頭都有認知失調的心理機轉,目的都是為了消除那種做錯決定的不適感。那跟判決有沒有被廢棄沒有關係。
重點在於,不願意「自證己錯」是人之常情;被告踏進法院,如果看到又是同樣的法官,會對法院的公平性升起懷疑之心,也是人之常情。不要忘記,在歐洲人權法院的孟小姐一案裡,並不要求證明法官確實有預斷,只要證明被告的懷疑有其道理就行。
由於法官的偏見幾乎不可能證明,因此為了保障訴訟權利、貫徹公平法院,檢視法官迴避問題時,多半採行「看似偏誤標準」(the appearance of bias standard)[16]。「看似偏誤標準」就是從一個知情觀察者的眼光來判斷,法庭的運作裡有沒有什麼「誘惑」(temptation),可能使得法官無法真正持平地審判。如果有,那就是「看似有偏誤」,應當迴避[17]。而且,當迴避與否有疑義時,應當朝向「那就迴避吧」的方向解釋[18]。
我們看看《憲法訴訟法》第九條一到七款,大法官自己的迴避規則多麼寬泛,曾經參與原因案件的審判就要迴避,人際連帶範圍及於配偶、前配偶、以前工作的事務所律師。為什麼?大法官不能排除預斷嗎?大法官不能超越認知錯覺嗎?這只是抽象規範審查,大法官不能跳脫隧道視野嗎?
其實這就是「看似偏誤標準」的意思。它是一個昭告天下的姿勢:大法官對於公平法院原則是多麼的重視,多麼的謹慎,因此即使只是瓜田李下,亦不容忍。
用「看似偏誤標準」來看便很清楚:根本不應該把案子分給已經審過的法官。在二審,這是法律保障不足;在三審,「連身條款」甚至系統性地全面製造這種不公平審判,並且違背法定法官原則。審級制度的設計初衷,就是讓不同的法官運用各自的思考與判斷,激盪出一個比較接近真相的結果。重複用同樣的法官違反了這個初衷,架空審級制度,使得同一法官的意志持續地決定這個案件的結果。
「連身條款」的擁護者一向主張,連身是為了防止最高法院浮濫發回,「原股法官總不好意思變來變去」。此次聲請釋憲的死刑案件全部都是連身條款之後的案件,更十一審、更十審的亦所在多有,顯然連身條款不是一個有效的手段,原股法官變來變去也沒有不好意思。《刑事妥速審判法》規定羈押八年[19]之後一定要釋放被告,才是釜底抽薪。何況,犧牲被告得到公平審判的權利,以換取迅速審判的權利,是何等荒謬的交易?那就好像醫生跟病人說:「如果我幫你把神經一條一條接回去,你就可以保住你的手指。不過,你應該很想趕快離開我的手術台吧?所以我幫你把手指切了!」
本案的關係機關一致主張把迴避門檻拉到最高,與前述歐洲人權法院及憲法法庭的「看似偏誤標準」背道而馳。刑事廳認為「法官迴避即意指更換承審法官……[20]」,並引用學者薛智仁、李佳玟的見解佐證,擔心法官迴避制度如果廣泛使用,會縱容當事人藉機挑選法官,造成社會對法庭的不信任。這與我們的主張風馬牛不相及,我們主張案子一開始就不要分給重複的法官,因此自然沒有「更換承審法官」的問題,更沒有「當事人藉機挑選法官」的問題。我們認為應該像德國在《刑事訴訟法》第354條第2項直接規定案件發回高等法院時不可發給同一庭,或日本《刑事訴訟法》第20條第7款直接規定曾參與原判決的法官不得執行職務。
——值得強調的是,德日的情況並非如專家與關係機關所言,法官重複也沒關係;而是他們正本清源,在分案的時候就已經過濾了。不是「重複時不需迴避」,而是「根本不會重複所以沒得迴避」。
最後,有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但是很多人都沒看見:死刑是不一樣的。此次釋憲併案眾多,多數學者與機關意見自始至終沒有提到死刑,彷彿死刑可以視同所有其他刑罰。在憲法法庭的規劃裡,「二審重複」的問題直接分配給另一案,彷彿死刑案件面臨的二審重複問題可以由非死刑案件「代表」回應。當然不行!死刑剝奪被告的一切權利,並且是不可回復的,因此應以最嚴謹的程序給予獨特保障(unique safeguards),絕對不是「比照」非死刑案件的程序或審查標準就可以令人滿意。說是這麼說,但是此次釋憲案眾人的忽略,正顯示那些「死刑要特別謹慎」的折衷說法,往往只是蒼白的自欺。
自七〇年代至今,美國法界確立了「死刑不一樣」(Death-is-different)的法理,為死刑案件備下更嚴謹的程序。與其他微罪相比,死刑判決裡的量刑十分重要,這樣極端的刑罰需要堅實的證據才能支撐其合法性。美國第七巡迴法院指出,「審判的論罪階段是客觀的,用冷硬的事實來了解究竟發生過什麼事;但死刑聽證卻有一大堆主觀證據。量刑減輕因素的證據通常是證詞,讓我們知道被告在人生中忍受了什麼樣的摧殘,或者他本來可以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21]。」這個觀察在近年台灣的死刑審判裡也成立:自2012年起,最高法院已決定死刑案件都會開庭做量刑辯論,2018年又提出「量刑前社會調查」;死刑案件在台灣最高法院的審理,和美國一樣是充滿主觀證據的,要評估的不僅是犯罪之「事」,更是犯罪的「人」。在此次訴訟資料中,刑事廳卻主張隧道視野只會侵襲事實認定的部分,最高法院是法律審,比較不受影響,所以法官重複也不會有偏頗[22]。這個主張一方面對於隧道視野與認知錯覺的理解不正確,亦未見引註,不知何來異想;另一方面也不符合死刑審判的實務。最高法院在其他案件原則上不開言詞辯論,或許可說是「純法律審」,但死刑案件在最高法院絕對不是純法律審。刑事廳是主管機關,仍然犯下忽視死刑特殊性的錯誤。
死刑是不一樣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雖然在Liteky v. United States一案中判決法官無須迴避,但該案與台灣死刑案件至少有三個不可比擬之處。其一:那是輕罪。其二:那雖然是同一被告、同一法官,但不是同一案件。其三:美國法官與台灣法官在法庭裡擔任的角色很不同,台灣法官負責認定事實,而美國法官處理的是程序與裁量,由陪審團認定事實,只有少數「法官審判」(bench trial)例外;Liteky的後案是有陪審團的。美國案例中,或許Williams v. Pennsylvania更有參考價值,那也是一個死刑案件。與歐洲人權法院的立場類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判決中明白宣示,不是只有「偏誤」才侵犯正當法律程序,「有發生偏誤的風險」就已經侵犯正當法律程序了。
死刑是不一樣的!總有一天,人們讀到這一段歷史的時候會感到不可思議,會有一對純淨的眼眸與一張仰望的小臉問道:「那個年代的人明明已經知道法官也是人,也會犯錯,各種偏誤一大堆而且無法避免,卻還是堅持要有死刑,而且想出那麼多古古怪怪的理由!他們為什麼那麼想殺人呢?」
此 致
憲 法 法 庭
中華民國111年10月20日
法庭之友 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代 理 人 張娟芬
代 理 人 李念祖
|
本研究的操作程序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