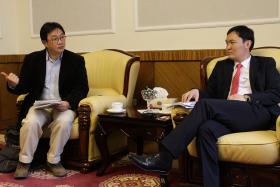倡議與行動
這裡會有廢死聯盟的新聞稿及倡議行動。
二二八68周年談蒙古廢除死刑
二二八68周年談蒙古廢除死刑
吳豪人
法國前司法部長Robert Badinter在『為廢除死刑而戰』中曾經提到:
「在支持死刑與反對死刑的兩派之間,各種論據都已經交換窮盡。做出廢除死刑的選擇已經完全是一個道義範疇的問題,但是,做出廢除死刑的決定則是政治性質。整個問題就在這裡。」
諸如廢除死刑等艱難的「決定」(而非選擇),乃一國政治意志的展現,甚至也等同於該國政治領袖政治意志的展現。而且此等決定之艱難,只見諸民主國家。因為政治領袖的決定,必然伴隨失去選票的風險。在Badinter眼中,能夠不懼失去選票也要貫徹自我信念的政治人物,當然就是他的親密戰友,法國前總統密特朗。不過,在2010年的蒙古,甫上任七個月的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卻也不讓密特朗專美於前,開啟亞洲民主國家政治領袖之先河,正式宣布他廢除死刑的決心。
國土面積156萬4千平方公里(約為台灣的43倍)、全國總人口286萬8千人(約為台灣的八分之一弱)的蒙古國(Mongolia),除了近乎滑稽地、仍然被中華民國行政院蒙藏委員會所「管轄」之外,長久以來似乎始終不存在於台灣人「國際觀」視野之內。事實上,蒙古從共產黨(人民革命黨)專政轉型成為民主國家的時間點(1990年),與台灣的民主轉型時間點(1987年-)幾乎重疊,而且兩國的民主轉型均由威權時代的執政黨主導,也同樣的均為不流血革命,並透過普選,成功的政黨輪替。在這段期間,蒙古對於民主人權的追求,無論在憲法、國家體制與法治的變革,乃至於與國際人權標準的接軌,莫不全力施為,同時成效卓著。例如,就筆者所知,現任蒙古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是全世界政治領袖之中,唯一一位受邀至北韓訪問,而且在紀念演講中公開疾呼自由人權的重要性,並高呼「暴政必亡」的外國元首。在這場演講中,他也列舉了許多蒙古民主化之後的重要人權政績,例如開放黨禁、民主選舉、制定新憲、司法改革、非核家園等等。而其中與台灣相較之下,最具強烈對照性的,正是廢除了死刑制度,而成為東亞諸國之中,第一個廢除死刑的國家。
人類史上「最大的殺人魔王」成吉思汗,他的子孫「為何」義無反顧的廢除死刑?
我在2014年9月23日至10月2日之間,與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數位成員前往蒙古,進行實地調查。從結論而言,此行最大的「意外收穫」,是發現了「死刑存廢爭論並未撕裂蒙古公民社會。而政治人物也無需裹脅/屈從『民意』,或與『民意』對決」的現象。箇中原因甚多,族繁不及輩載。但是至少這個現象本身,卻間接的證明了:台灣(以及日本、美國等)社會的死刑論爭,無論正方與反方,在問題的預設上(=價值/信念的認識與信賴上)有多麼的特異。
2010年1月14日,額勒貝格道爾吉總統在蒙古大國會(the State Great Khural)所做的演說「The Path of Democratic Mongolia Must be Clean and Bloodless」,在亞洲人權史上,是一份不容忽略的歷史文獻。在這場對全體國會議員的演說中,額勒貝格道爾吉總統首先力陳「蒙古民主憲法的終極目標,在於捍衛自由與人權」,「而正是因為我們捍衛了憲法,所以才能夠成功地達成許多強化我國社會人權、自由、與司法正義的成果」。但是,仍然有許多未竟之功尚待完成。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蒙古憲法視為至高無上的人權──生命權的維護。接著,他列舉了八項廢除死刑的理由。
(I)赦免一條生命,並不等於免除其刑罰
(II)死刑之不可回復性(冤案之不可避免)
(III)死刑之濫用(轉型正義)
(IV)國家殺人(死刑)不但不值得讚美,反而是最為貶損人性尊嚴的刑罰。(並論及蒙古宗教與文化中的生命觀)
(V)廢除死刑才能與國際人權基準接軌
(VI)一個執行死刑的政府,沒有任何道德權利要求她的國民「相信你們的國家,對政府要有信心」
(VII)維護蒙古做為一個民主人權國家的國際聲譽
(VIII)死刑絕對無法遏止兇惡犯罪(犯罪者害怕的不是死刑,害怕的是正義與公正的審判)
以上八個廢除死刑的理由,有不少與台灣廢死者的主張重疊。比較顯而易見的,例如「死刑之不可回復性」「與國際人權基準接軌」「死刑絕對無法遏止兇惡犯罪」。其他的理由,縱使社會或歷史脈絡未必相同,大致上也可以在台灣的廢死論中找得到,除了理由(VI)──如果不是一個充滿政治道德感的政治人物,絕對說不出如此具有啟蒙主義精神的話語。這句話甚至遠遠勝過了Badinter所樂道的密特朗。因為密特朗的堅持,出於一個傑出政治家的個人信念,而額勒貝格道爾吉的堅持,卻來自於對人權普世性的全然樂觀。額勒貝格道爾吉並不是密特朗的仿效者,他更接近美國的開國元勛們。
然而,台灣與蒙古(甚或法國)最大的不同也正在於此:這八個理由,在台灣是由公民社會中的部分成員提出的;而在蒙古,卻是由民選總統在最正式的政治場合親口說出來的。換言之,蒙古(法國)的政治領袖做出了最艱難的政治決定,並且自負所有風險。因為額勒貝格道爾吉總統廢除死刑,是在第一任總統任期內。他仍然必須承擔連任之際選票流失的政治風險。事實證明,他通過考驗,並在2013年大選中獲勝,續任蒙古總統。相反的,台灣的政治領袖,則仍然龜縮在「民意」擋箭牌的後方,繼續嗯嗯啊啊的「聽您之言頗有理/可是我們不敢說/大概或者也許是/的確好像差不多/既然如此想必對/不過恐怕不見得/建議各位再研究/最好大家多斟酌/總之等以後再說/請問您意下如何」。
當然,額勒貝格道爾吉總統的廢除死刑政策,之所以能夠得到國會不分黨派的全面支持,甚至也未曾引起國民的反感而斲喪個人政治生命,其立論自有堅實的歷史、文化與社會基礎與共識。不過,既然是二二八專輯,在這裡我只想集中在(III)死刑之濫用,也就是蒙古的轉型正義與廢除死刑之間的關係。
根據日本法學家島田正郎的研究發現:無論是最重大的私人間加害行為,或對於所謂「公家權威」(國家體制)的反抗,「科以死刑,不許收贖」的規定,若對照蒙古歷代的法律制度變遷史觀之,幾乎都是外來統治者(清朝=中國、蘇聯)的片面強制規定,根本不是蒙古民族的傳統法,遑論傳統「法感情/法意識」。死刑的大量科處,來自嘉道年間的「中華=殖民宗主國法系」的強制。易言之,中華法系「罪大惡極,依律當斬」的死刑觀,在蒙古人的歷史經驗裡,依的是異族強權的律,當斬的大罪,也不過就是不聽中國的命令。所以所謂的「五族共和」,就蒙古乃至於其他的「邊陲民族」而言,也不過就是一段被殖民的歷史。而蒙古如此的歷史經驗,在1921年名為獨立實則成為蘇聯的附庸之後的、漫長的70年中,則繼續被傳承下去。
蒙古在1930年代,受到瘋狂整肅異己的蘇聯史達林主義影響之下所進行的大屠殺,其慘烈程度完全不遜於二二八。額勒貝格道爾吉總統堅決廢除死刑的第三點理由「國家對死刑的濫用」,指的正是這一段歷史:
「蒙古人已經受夠了死刑這個選項。歷史在已經明確揭示了這些事實:從1937年10月,到1939年4月,僅僅16個月之間,就由所謂的特別全權委員會51個法庭判處並執行了20474個蒙古公民的死刑。其中宣判最多死刑的單一法庭,竟判決了1228人死刑。而且有證據證明,其中包含8位女性。」「許多蒙古人都相信,有外國勢力介入這個大整肅行動。可見如果我們保有死刑制度,不僅會被國內力量使用,也極可能為外國勢力所使用。而絕大多數被鎮壓整肅的人民,當他們遭處決的時候,均是芳華正茂的年紀。」
「很明顯的,當時的政治與法律狀況並不能與今日互相比較。如今已有了巨大的改變。然而,死刑的本質並沒有改變。死刑,就是國家殺人。這點從未改變。在死囚之中,67%的蒙古公民都是20-40來歲的青壯年,而且他們幾乎都是初犯。」
而若根據1988年人民革命黨黨中央委員會總會的推估,這段時期被依「反國家罪」判刑確定者2萬5785人,其中被判處死刑者2萬39人。
易言之,死刑比例幾乎高達八成。蒙古國立大學法律系主任,曾經協助國際特赦組織蒙古分會進行蒙古死刑調查報告的刑法學家Bold Amarbayasgalan教授在接受筆者訪談之際,除了再次強調「大整肅」恐怖時代的經驗形塑了蒙古人的「死刑觀」之外,還特別提醒:
「不要忘了,1930年代的蒙古只有100萬左右的人口,卻有兩萬以上的人遭到國家處決。換句話說,幾乎每家每戶都有受難人,每家每戶都是被害人家屬」。
 如果根據另一個數據,1930年代蒙古的人口其實只有73萬8千人,那麼受難人的比例就更為驚人。而且這個死亡數字,還不包括被屠戮的17000個僧侶(所以蒙古佛教界可是強烈支持廢死的喔)。在此,我們可以理解到,轉型正義的反省機制與蒙古廢除死刑動機之間強烈的因果關係。但是,蒙古對於轉型正義的反省,並非純然的「自省」,同時也與其地理政治學的處境息息相關。
如果根據另一個數據,1930年代蒙古的人口其實只有73萬8千人,那麼受難人的比例就更為驚人。而且這個死亡數字,還不包括被屠戮的17000個僧侶(所以蒙古佛教界可是強烈支持廢死的喔)。在此,我們可以理解到,轉型正義的反省機制與蒙古廢除死刑動機之間強烈的因果關係。但是,蒙古對於轉型正義的反省,並非純然的「自省」,同時也與其地理政治學的處境息息相關。
首先,全世界的蒙古民族如今大約有800多萬人口,但卻分散在三個國家裡──半數,也就是400萬居住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蒙古自治區(而且自治區內漢蒙人口比例為五比一,蒙古人反而成為少數民族);另有80萬人居住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等地;居住於舊蘇聯(如今俄羅斯領)的布里亞特地區的有80萬人、以及獨立蒙古國的280萬人。前述總統演講中所謂的「外國勢力」,就獨立蒙古國國內史而言,指的當然就是蘇聯。蘇聯正是繼中國之後,強制蒙古民族必須「習慣」死刑制度的第二個強權。然而,如今雖然蘇聯已經瓦解,但圍繞蒙古的強鄰,仍然是不改其極權體制,而且仍然保有死刑的俄羅斯、北韓與中國。何況除了北韓之外,在中國與俄羅斯國境之內,還有形同人質的600萬蒙古同胞。
其次,如同田中克彥所言,要理解今日蒙古國家與社會,就要注意到他們心中一道揮不去的陰影:只要外來強權高興,管你是蒙古人民愛戴的首相或將軍 ,隨時都可以任意將之擄劫至莫斯科處決,更別提一般國民了。
「這種權力,蒙古人(蘇聯操控的蒙古傀儡政權)也許也使用過。但是至少不是蒙古人自己發明的。假如沒有蘇聯這個體制,蒙古人根本不會知道有這種權力,遑論使用。……而且這種陰影,對於中國內蒙古的蒙古人同樣適用。」
例如在土改運動中,內蒙古的牧民(包括漢人地主)估計就有200萬人遭到中國共產黨殺戮。而內蒙的蒙古人,光是在文革時期的1968-69年就有47000人遭到屠殺,70-90年則有7000人被屠戮。
田中說:「對蘇聯而言,或者對俄羅斯人而言,這些(蒙古人的)悲劇根本是不值得記憶的歷史小插曲(對於中國也一樣)……然而,蒙古人卻永誌不忘。」
這兩段話道盡了大國/帝國/主流文化/主流社會的歷史敘述可以多麼扭曲,以至於一廂情願的也輕率地扭曲他人的歷史。就此點而言,連續受到日本與中華民國統治的台灣原住民一定深感共鳴,特別是:他們也沒有死刑。而且,從國家/民族規模觀之,似乎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越是小國寡民,死刑越無法存在。輕忽國民生命的,往往都是大國與帝國。所以蒙古的轉型正義,肩負的責任正是還原自家歷史,從而放棄遺忘、全心記憶。鄭南榕的名言「我們是小國寡民,但我們是好國好民」,居然在蒙古得到了印證。
 總之,在這些「惡鄰」漫長無止境的環伺之下,今日蒙古的政治精英採取的自保之道,不但不是同流合汙,反倒是徹底的引進普世性的啟蒙價值,不斷的追求民主化與深化人權與和平。他們既要擺脫「中華法系/文化」,也得擺脫「俄羅斯=蘇聯法系/文化」。在此意義之下,廢除死刑當然是民族自保邏輯的必然推演結果。廢除死刑,正是最雄辯的「脫華/脫俄」宣言,甚至還能一舉擺脫狹隘的中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如果再把蒙古的「非核家園宣言」考慮進去,蒙古的整套民主獨立策略就越行清晰可辨了。蒙古身處中俄兩強國之間,早在俄軍退出蒙古之後不久,便宣示本國為「非核武地帶(Nuclear Weapon Free Zone)」。此舉不但直接表明了中俄若有衝突時,蒙古的中立立場,更因此獲得國際社會肯定「乃強化區域和平與安全保障的重要因素」(聯合國總會決議53/77D.1998/12/4),因此被認為是類似日本憲法第九條的和平反戰宣示。此後蒙古不但禁止興建核能發電廠,現任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更力抗美日壓力,於2011年9月9日發布總統命令,禁止在蒙古國內建設核廢料儲藏所。反而是「進步的強國」「全民反廢死」的日本,不單無視三一一慘劇的教訓,甚至已經箭在弦上的準備廢棄和平非戰的憲法第九條了。
總之,在這些「惡鄰」漫長無止境的環伺之下,今日蒙古的政治精英採取的自保之道,不但不是同流合汙,反倒是徹底的引進普世性的啟蒙價值,不斷的追求民主化與深化人權與和平。他們既要擺脫「中華法系/文化」,也得擺脫「俄羅斯=蘇聯法系/文化」。在此意義之下,廢除死刑當然是民族自保邏輯的必然推演結果。廢除死刑,正是最雄辯的「脫華/脫俄」宣言,甚至還能一舉擺脫狹隘的中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如果再把蒙古的「非核家園宣言」考慮進去,蒙古的整套民主獨立策略就越行清晰可辨了。蒙古身處中俄兩強國之間,早在俄軍退出蒙古之後不久,便宣示本國為「非核武地帶(Nuclear Weapon Free Zone)」。此舉不但直接表明了中俄若有衝突時,蒙古的中立立場,更因此獲得國際社會肯定「乃強化區域和平與安全保障的重要因素」(聯合國總會決議53/77D.1998/12/4),因此被認為是類似日本憲法第九條的和平反戰宣示。此後蒙古不但禁止興建核能發電廠,現任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更力抗美日壓力,於2011年9月9日發布總統命令,禁止在蒙古國內建設核廢料儲藏所。反而是「進步的強國」「全民反廢死」的日本,不單無視三一一慘劇的教訓,甚至已經箭在弦上的準備廢棄和平非戰的憲法第九條了。
我認為這樣的日本,根本就是已然死滅的幽冥國度,只不過日本人不知道自己已經死了。死者不知自身已死,原來不是宗教寓言。對於活死人而言,原來黃泉之水如此甘美。
理解了上述蒙古的地理政治學處境,我們才能認識到:蒙古政治菁英的人權政策,多麼具有前瞻性。他們甚至已經將視野擴大到未來的民族統一。只是這個統一,並不依恃暴力,卻奠基於人權。因為,還有將近七成的同胞,仍然居住在既不民主也無人權的近鄰帝國裡──而且,這兩個帝國至今仍然使用死刑威脅蒙古同胞。
蒙古與台灣同樣的經過非常類似的民主轉型。甚至可以說,蒙古的昔日歷史與現今的地政學處境,就是台灣的昔日歷史與現今的地政學處境!蒙古政治與法律菁英一再向我保證:「我們不會走回頭路的。因為我們的新憲法架構下的國會/總統制的設計,讓獨裁體制與外國勢力無隙可趁。而死刑也不可能死灰復燃,因為1936年的那場近乎種族滅絕的大整肅,讓我們深深體悟到生命權的重要性。蒙古人口太少了,每一條生命,都彌足珍貴」。台灣也曾經歷過二二八大屠殺、白色恐怖以及漫長的獨裁體制,但似乎沒有政治菁英曾經因此而「深深體悟到生命權的重要性」。台灣的民主轉型,雖然未曾流血,但國民付出的代價,也未必便遜於蒙古。但是我們的憲法歷經七次修改,卻從未增修第二章「基本人權」,大多數國民也仍欣然擁抱死刑。
台灣人口太多了嗎?
台灣的憲政體制,已足以令「獨裁體制與外國勢力無隙可趁」?
接下來就要爆粗口了,就此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