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恩主公案未被看見的另一面
文/詹斯閔(廢死聯盟志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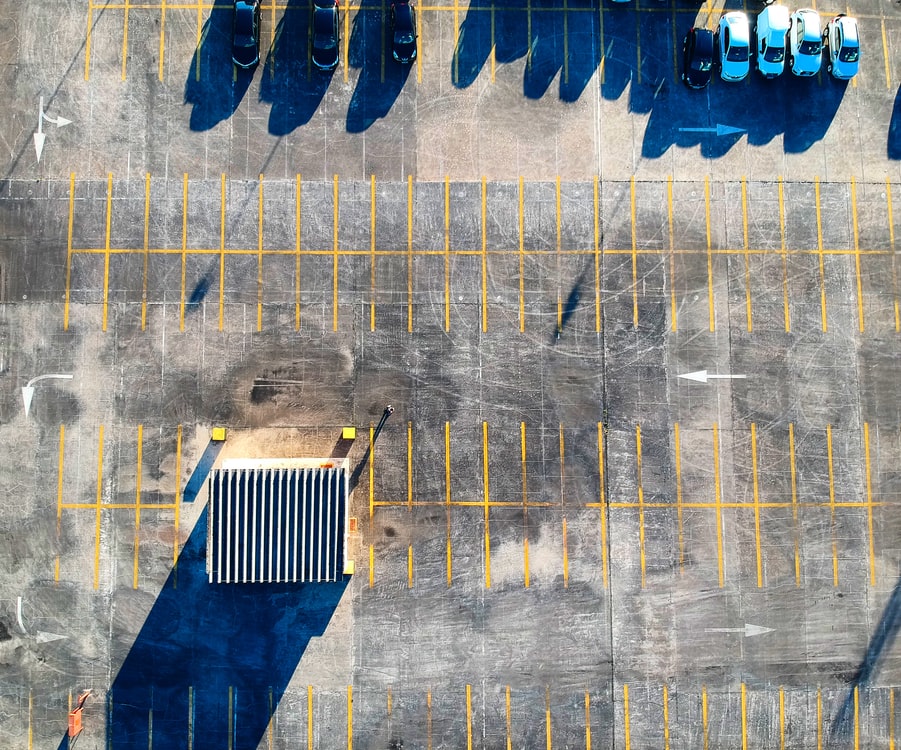
福爾摩沙高速公路行過一個彎,交流道下去,凌晨暗景裡,三峽恩主公醫院透出一窗窗玻璃白光,詭靜照著空曠的停車場。車上兩個肉身疊躺,氣息剛止,魂魄還未散盡。兩人是被棄屍?抑或是被苦亂慌慌地送來急救,無奈抵達時已太遲?答案只能任由道德評判的眼,事後安上詮釋。
2012年,台灣剛經歷總統選舉,由馬連任,夾以媒體壟斷旺中案風火不斷。但邦國事遠,沈文賓只為老婆離家出走一事煩心。12月10日晚間,他帶著弟弟沈文夏出門,綁來妻子的女性朋友和當時在場的另一男子,希望逼討出妻子下落。產業道路盡頭,難言的憤怒在灌溉溝渠裡發臭,沈文賓出手將人按進圳底,一回神才驚覺兩身已浮上水面。夫妻爭吵看似尋常,為何這次他非得找到她不可,繼而將怒意傾嫁於無辜的旁人?沈文賓說,他只是想讓太太出席父親葬禮;這是她身為長媳的責任。
婚姻裡的傳統丈夫
妻子為何離家出走?夫婦感情好嗎?要更精準的釐清這些疑問,或許得先從他們如何相識相處説起。妻是國中隔壁班同學,沈文賓進少年感化院時分手,出院後他主動追回。沈坦言,女人好壞就是看身材好不好、能否帶出遊同歡,這一任女友和其他對象相比沒什麼不同, 或許因為當初是女方主動提分手的,他心底有種被甩了的不甘願。
相處懷孕了兩人便順勢結婚,「老婆在家打電動顧小孩,我跟她說不用出去做。」沈文賓似乎認為有養家就是個稱職的男人。婚後兩人偶有衝突——妻感覺沒有自由,這是爭執的恆常主題——沈覺得自己沒有強壓任何限制,白天不必上班的妻就是個閒散主婦,他只希望孩子放學和自己下班後妻該安守家戶,乖乖待著別再出門;身為當家之主,這樣的要求並不過分。沈不願意幫妻買車,擔心她開車載人四處跑。
單看他們相處,就是尋常伴侶,難免有些需要磨合。從沈文賓的言談判斷,他也絲毫不感覺兩人交惡;儘管沈的妹妹曾提及,看過嫂嫂玩愛情交友網站。若從另一面來想,這般婚姻裡的女人能自足快樂嗎?更艱澀的問題是,女人在這樣傳統關係裡的不自由不快樂,男人有辦法理解嗎?不曉得沈妻渴求著怎樣的獨立自主,但非常確定的是,父輩和俗眾只教導勇敢威武,沈文賓在親密關係裡只曉得當個大男人,主宰掌控。而他也缺乏任何柔軟工具解決困境:妻子離家後沈曾上門談判,她說到某次吵架被他踹了一腳,當下他立刻拿起刀子劃手腕,說是要以血來還;他送上的不是溫柔道歉,不是擁抱和安慰。
長男長孫的承擔
這一個典型的陽剛男人在何種家庭長大?說起自己身世,沈文賓一開口便是驕傲:「我爸爸有兩個老婆。」大媽小媽同住一屋簷下,一起撫養各自生的小孩共六個,同時一邊在家擺檳榔攤。兩個女人一輩子相安無事,周周輪值煮飯,就算偶有冷戰,開檯仔間經營賭博電玩的爸爸總能擺平。沈文賓擔演長男,父親忙碌在外時往往吩囑孩子們「找阿兄」:弟妹不時借車載女友或借錢花玩。身分證P開頭,沈氏宗祖落土雲林,「回去掃墓才知道家族有一兩百人!」伯父沒生半個子,沈文賓肩上同時承著長孫重擔。
華人儒教文化裡,長男長孫有一套已寫定寫死的人生腳本,這也主導著他腦海裡的婚姻家庭風景,以及他認知裡婚喪禮俗的該與不該。父親逝世是何等隆重哀痛的家族大事,長媳該挽髮斂身,垂手立於祭壇旁側,帶領眾親完成「家屬答禮──」那綿延戚絕的次次回拜。偏偏新世代強調個體性,不是每個家族成員都肯續演舊有職分。沈文賓從千千萬萬個長男長孫手裡繼承了傳統,卻不懂該如何與現代交鋒。「媳婦怎麼沒來?」親族耳語窸窸窣窣囓咬著他的理智,腐噬著他引以為傲的兄長權威。
知識階級決定想像
是的,性別框架和家庭包袱不只他有,難以勝數的生理男性都困滯其中。其他人沒因此犯罪,為何就他有?父親事業難免要混要喬,黑和暴力就像沈家客廳裡的破沙發,坐久了,孩子們便以為每張椅子都會露出敗爛棉絮。退伍後沈文賓開始從事討債工作,嚇嚇人的暴力號稱一切合法,實則游走法律邊緣。遇上了事,逞兇自然是他意識裡第一順位的解決工具。幫派比誰凶、比誰剛強勇猛,如此環境更不可能引導他探索柔婉感受,自察種種憤怒背後,誠實的無助自卑和惶恐。
若是愛讀書,早就不會混了,但開放靈活的性別觀和情感教育較易見於菁英知識圈──婚姻諮詢和性別平等這些字眼,無論如何不屬於沈文賓的日常──討生活都不容易了,誰談這些。他很自然地跟隨主流,依循舊慣對婚姻和家庭的設定。
沈文賓是害了無辜沒錯,可追究責任和釐清原因從來是兩件事。看似「正常」的一段婚姻為何發展至此,衍生怒和罪?善惡彼端,他真有健整的知識和自由,用以面對茫雜龐大的感情婚家議題?值得從另一面想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