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權力相遇—張芳馨案法庭觀察心得
編按:2018年12月11日,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大廈第二法庭召開107年度上重訴字第43號審判程序,主流媒體以水泥封屍案稱之,本文為其法庭觀察心得。2019年2月,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本案無期徒刑定讞。
文/ 王俞茹(廢死聯盟實習生) 封面圖/ Tyrso
不久前,我親自在法庭的現場,觀察了一場殺人案件的審判。
時隔一個禮拜後,我可以說,真實地去看一場審判,會把腦海中所有沉寂的、思考過的、聽見的、看過的關於死刑各種面向的事情、理論,重新在腦中強烈且反覆地翻滾過一遍又一遍。
在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實習近三個多月的時間,不論是站在幫忙抑或是觀察的角度(觀察廢死聯盟的工作、舉辦的活動,甚至關注死刑相關議題的許多工作者的論述、行動),都讓我在關於死刑、廢除死刑、加害者、受害者這些交織複雜的面向中,擁有更多思考與反思的可能性。

這些思考與思辨的動力,都從在大學時修習過關於死刑反思的課程之後,就開始累積並漸漸加深。但是所有思考都可能因為沒有再更多切身體會、看見的機會,而讓那些曾經深深觸動自己,烙印在心頭的問題意識沉寂下來,好像從曾經高速旋轉的思考漩渦中慢慢抽離。
但是,就在這個天色昏暗,下著陰陰細雨的星期二早晨,我獨自一人坐在高等法院刑事庭第二法庭後方的旁聽席;時間是早上十點整,被告和三位辯護律師已坐在席上。聽不見外頭雨聲,只聽見檢察官跟鞋踩踏著地板,以及三位法官腳步匆匆步上台的聲響。在這個空間的所有人都因為一起殺人事件,在星期二的第二法庭上,與權力相遇、激辯。
幾乎沒有實際置身在法庭現場旁聽觀察過的我,過去對於法官模樣的想像,是透過他人書寫,又或媒體報導的重大矚目案件中所呈現的樣貌;而那些關於死刑審理判決過程中的法官,好似有些冷酷、沒有溫度的權力執行、詮釋者。
然而,這次親眼見到的審判現場,審辦長無論在告知被告權利或詢問被告問題時,陳述中都帶有一種溫厚感,這對我來說,這是和自己的想像很不同之處。

儘管是自己的主觀感受,但我相信人與人之間透過話語傳達出的態度與情緒是能強烈共感的。我認為那樣的溫厚,在於給此刻的法庭場域中,實際上握有權力與話語權最小者—即被告(即使形式上言明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也能夠掌握自身言說、為自己辯護的權利,而非懼怕於這個名為公正審判的權威場域,使其變成一個最渺小、無法言說的存在。
審判過程的前半段,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被告的答覆。她在回答法官問題時,都是用簡單的,甚至是不太能夠清楚表達前後脈絡意思的隻字片語回答。但因為書記官必須馬上做紀錄,程序也不斷地進行下去,所以我感覺,似乎是以法官不斷接續問題去連貫被告語句的意思,書記官則依此應答為據,打出一段完整意思的句子。
我們可以說,或許因為被告教育程度不高,又或許因為被告在法庭上被詢問時可能緊張的情緒,沒辦法讓她能夠說出更清楚、完整能表達自己意思的表述。然而,事實就是,法庭這個場域實際上沒辦法讓所有疑慮獲得解答,沒辦法細細詢問被告剛剛沒表述清楚的句子是什麼意思?為什麼這麼說?還想要表達什麼?

若以一場表演做為比喻,被告像是主角,而且是唯一經歷過所扮演角色的真實人生。法官、檢察官與辯護律師,則是預習了主角的人生,再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排演之後,上場試著重新詮釋這位主角的真實故事。但是,所有的重新詮釋都是論述的過濾,在這個名為法庭的表演舞台,當一句臺詞被言說而出,就同時有另一段事實被掩埋在黑暗中。
第一位辯護律師上場,詮釋著重於對被告生命故事的陳述,其訴求是希望能從無期徒刑改判為有期徒刑。
辯護律師說明被告生活上的辛苦、對第一段婚姻的失望以及對未來生活的期待等,因為這些生命的辛苦與委屈,好像就這樣一次地傾瀉於這次殺死和自己同住小姑的行為。
緊接著是檢察官的論辯。
檢察官說,這樣的論述會不會給社會大眾一個錯誤的印象,是不是今天只要我有不美滿的生活、生活的壓力,我就可以用殺人的行為傾洩在一個人身上?此時,檢察官開始用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把自己當成被害者,站在被害者的立場,陳述遭受殺害對待時心裡的呼喊以及內心的疑問和委屈。

我認為這兩段論辯重點都在於以第一人稱的視角打動人的情緒,雙方都盡可能站在那個我們無法回到的過去、無法親臨的角色位置做陳述、辯護。但事實是,我們都無法真正的為誰代言。
當辯護律師陳述被告生命故事何以可能為殺人動機、檢察官以第一人稱替受害者發言時,我們不知道這樣生命沉重的分量到底有多重,是否合理以此作為減低刑罰的理由。我們更不知道這起殺人事件的導火線,對於被告是多麼的沉重、足以燃燒?相對的,對於已故的受害者又是多麼的不解和委屈?
對於檢察官的提問,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我想,在可以清楚做選擇的情況下,我們大多不會希望自己親手,用殺人這種不可回復的方式,去傷害一個和自己一樣,擁有能動力、思考能力、感受痛苦能力的生命
我認為,或許在此刻訴求減刑的審判當中,我們更應該思考的是刑罰的意義。為什麼判處死刑?為什麼判處無期徒刑?訴求減為有期徒刑和罰金的合理性及意義?這個想法,在第二位辯護律師的論辯中,我很清楚地聽見正是針對刑罰界定的討論。
辯護律師舉了多個同樣為殺人的案件為例,比較各個案件與本案的條件與判決結果之差異,希望據此作為減刑的論辯依據。

從律師整理的比較表格中就可以很清楚看見,我國法律在殺人罪刑裁量上的恣意性、不確定性。律師一一比較說明,儘管述說的態度溫和,卻也透露著強烈的質問:我們的法律、法官對於做出怎麼樣的判決處分,是說不出原因、不可靠且恣意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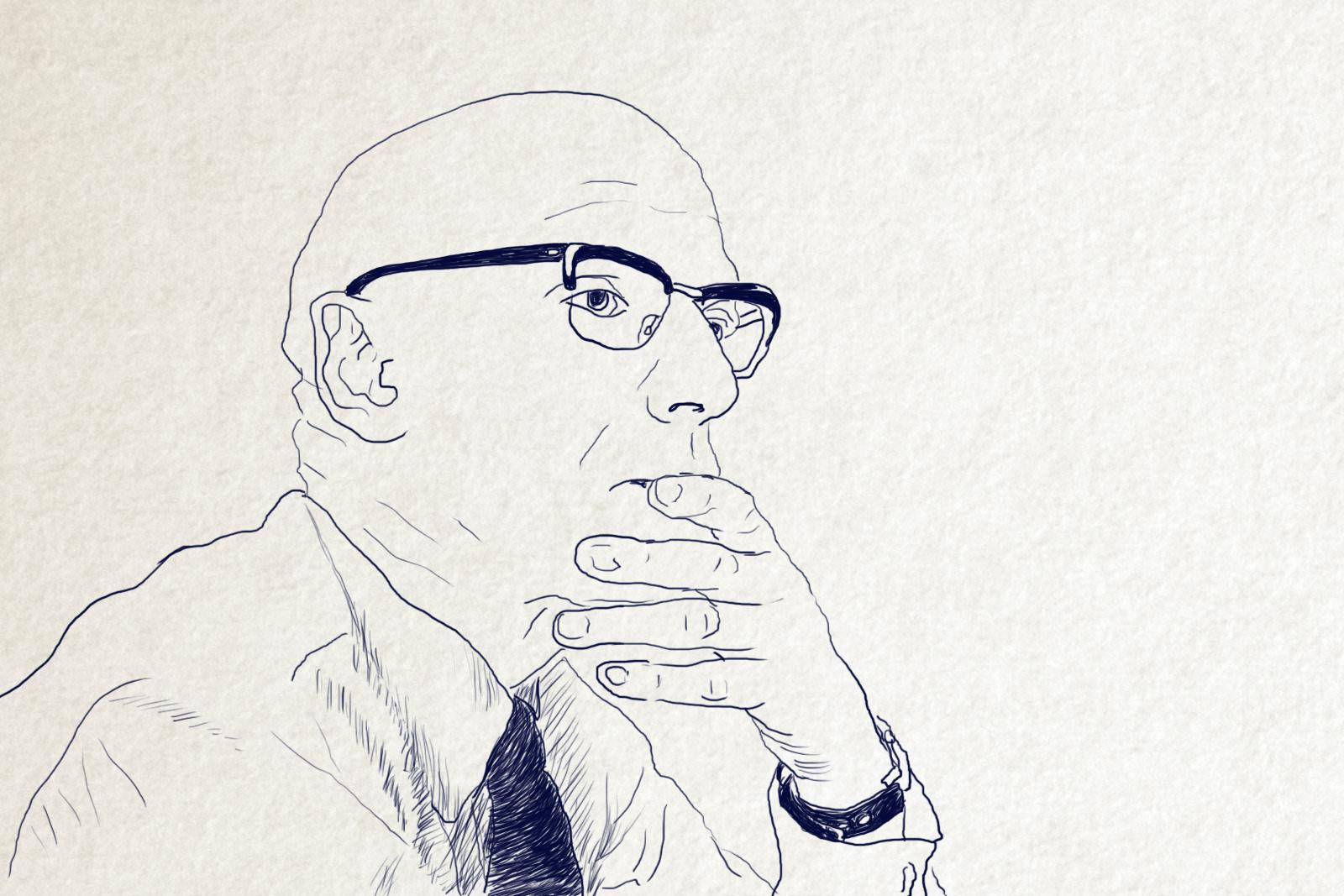
在Michel Foucault《聲名狼藉者的生活》中是這樣描述聲名狼藉者的:「這些生命本來能夠、而且應當處於無名的黑暗之中,然而,與權力的一次偶然相遇,卻把他們從黑暗之中拖曳出來」。
被告因為殺人的違法行為,使他身在法庭之中與權力相遇,其言說、犯刑和生命故事被記錄與詮釋。「只有在剎那間與權力接觸時,他們才留下了自己存在的痕跡」,一如Foucault所言。
如此與權力共存形式所留下的話語、文字紀錄,沒辦法讓我們看見個人全部生命狀態的面貌。但是在這樣被拖曳出的故事、言說之中,我們可以選擇恣意的裁量、判刑;也可以選擇藉此思考、深入反省更多關於生命處境、關於倫理,甚至刑罰意義的可能性。
一篇殺人案件法庭觀察的紀錄與思辯,所有陳述方式、語句脈絡,是經過一段時間對死刑議題與相關理論的觀察、閱讀及思考沉澱下的過程。作為過程,必然會有缺漏,也會有所變化,就像是本案也還在審判的過程之中。
希望每一個過程都是批判的,積累著思考與擁有改變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