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殺人案件背後被遺棄的世界—《求其生而不可得?》書介
文/吳奕靜(廢話電子報特約記者)
求其生而不可得?
「求其生而不可得」一語,出自歐陽脩提及其父的判案態度,說明其父親總是會努力找到不將人判死的理由,遍尋不著,不得已才將人判死。但若在台灣的判決書中查找會發現,這句話常用於法官決定做出死刑判決時,彷彿法官對犯罪者無可奈何道:「你都犯下滔天大罪了,連我也找不到你求生的理由。」但,真的是如此嗎?
法律扶助基金會與廢死聯盟共同出版書籍《求其生而不可得?台灣殺人案件背後被遺棄的世界》,由長期關注各項人權議題的記者謝孟穎所寫,前半部以六起殺人案件被告人生原本的樣貌,試圖迫近犯罪者犯案前所歷經的生活日常,探問「變成殺人犯前的他與她」;後半部則訪談不同案件中擔任法官、律師的看法及觀察,以及案發後被害者家屬、加害者家屬的心境,進一步追問:真的只能殺人嗎?殺人這件事在真正的意義上是什麼?這些問題不只是對犯罪者問,也對法官問、對動輒喊打喊殺的整個社會提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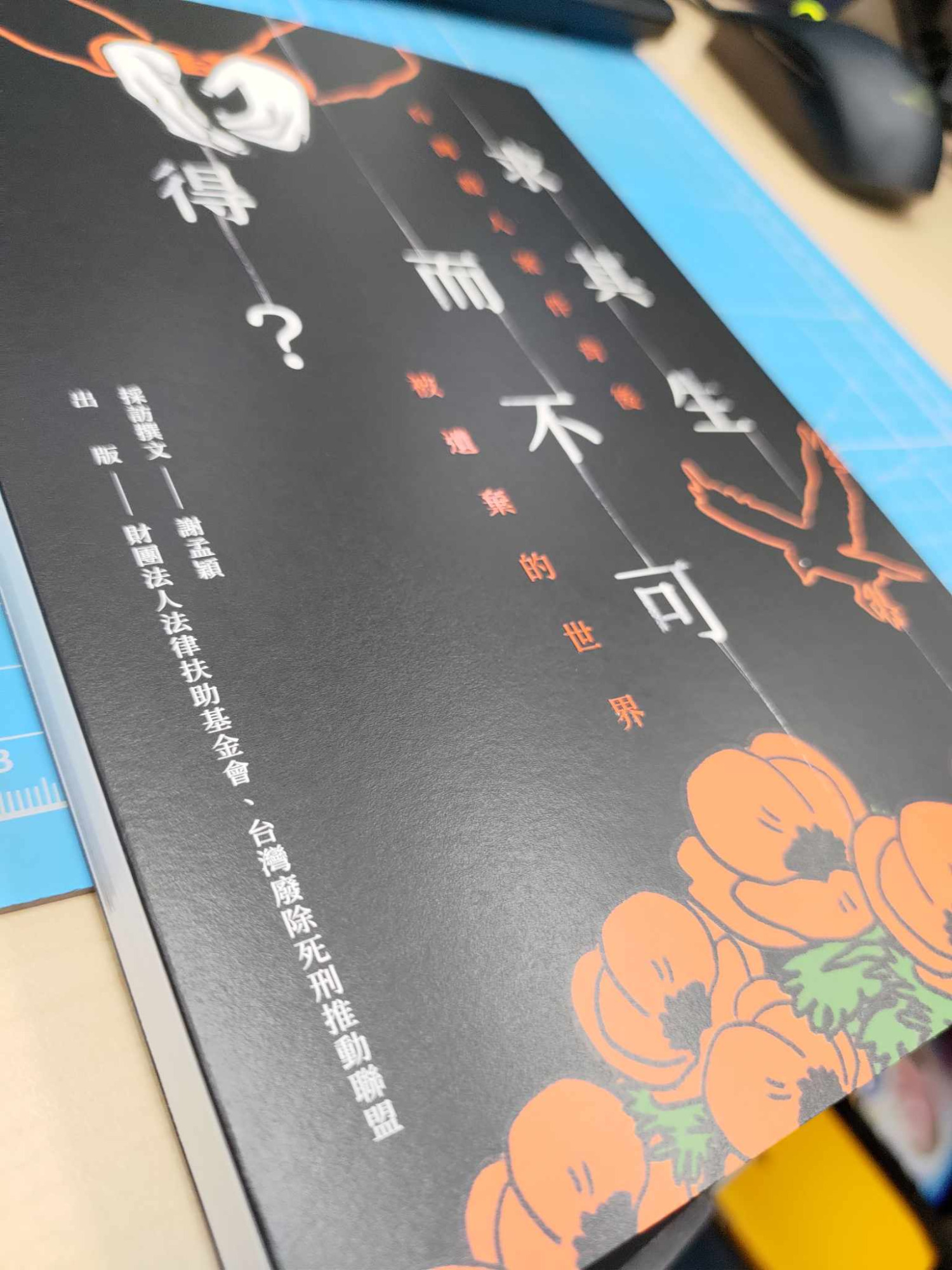
被遺棄的世界
《求其生而不可得?:台灣殺人案件背後被遺棄的世界》一書作者謝孟穎在座談會中分享,或許大眾總會在新聞中看見犯罪者極其荒謬的言論「殺一、二個人不會死」或者毫無悔意的冷笑印象。但其實孟穎的受訪者當中,有許多重刑犯在犯案時,甚至犯案後對自己的生命根本不屑一顧,覺得「反正自己沒救了,死一死算了」以為自己在犯案當下可能會被警察當場擊斃,或者法官判決死刑後就會馬上被執行死刑,希望透過死刑了結生命。他們對於整個司法審判制度非常陌生,也沒想過討好法官(甚或是單純基於法律義務為自己辯護的律師)。
書中第一個案件是犯下台南湯姆熊案的曾文欽,當時孟穎讀了胡慕情寫的〈血是怎麼冷卻的〉一文,她想試著讓大家知道十年後,重刑犯曾文欽過著什麼樣的日子。「他說想要看《烏龍派出所》,我本來以為很好買,後來找一找才發現,因為2016年《烏龍派出所》已經完結,在一般市場上不是這麼好找到。當我告訴他這件事的時候,他好像突然有點惆悵黯然。這給我一種感覺是,他很喜歡的東西其實在世界上已經慢慢要消失了。我們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在發生,但他在裡面的時間卻好像一直在停滯,這讓我開始對監所的生活有了真正的理解。」
另一位已經病死獄中,犯案時76歲的獨居老人郭旗山,他舉目無親,新聞報導敘述他放火燒死了曾對他伸出援手的村長一家,但事情真的就只是這樣嗎?前冤案死囚謝志宏曾經和郭旗山在監所裡是室友,面對年事已高又「殺害恩人」的老人家,監所裡的「同學」們都不知該怎麼與他相處,也從來沒有家人朋友會來接見,少數幾次廢死聯盟要接見時還被拒絕,事後才得知郭旗山當時身體狀況不佳,連走到接見室都有困難。根據卷證,郭旗山在案發後逃跑15天才被找到,警察找遍當地所有公共設施,但在這段期間他卻一個人搭著客運走透各地,無人知曉。謝孟穎認為,這似乎反而說明了這個人在整個社會沒有任何的連結,只是虛無的流浪而已。
郭旗山犯案是基於貧困、街友身分或被遺棄的感受嗎?什麼誤會讓他犯案?我們現在已無從得知,因為判決書只交代他是如何犯案,然後論罪定刑。這是另一個被遺棄的故事。

你說的小事情是我的生活
蔡英文政府任內執行的第二位死刑犯翁仁賢,看似是不知感恩的啃老族,但他為自己生計所做的努力卻沒有機會被正視,也無法符合家人和社會的期待。翁仁賢曾經想要養狗去賣,但他裝飼料的瓶子被哥哥拿去裝農藥沒洗乾淨,狗便死光了;他也曾養育孤挺花、種蔥,卻遭到家人朋友隨意踩踏、開車輾過。法官在判決書中評斷這些事情是日常生活中的小摩擦,不應該歸納為殺人動機,但是對抱持著極大恨意向家人潑灑汽油、縱火的翁仁賢來說,可能正是這種長期被忽視的「小事情」累積出無法阻止的動機。
孟穎過去書寫武張孝慈案、特宏興368號外籍漁工殺人案件報導時,倘若寫出當時雇主對被告的虐待、強迫勞動等不人道待遇,隨之而來就有另外一種評價,認為被告是「殺得好、活該」。孟穎認為,寫出報導並不是為了讓公眾認為自己可以去評價誰才是「更該死的」,不能都活下來嗎?理解殺人案件的脈絡,並不等同於鼓勵人可以隨意的把壞人殺掉;也不會因為一個人殺的是壞人,好像就比較沒有關係,這顯示出人們實際上對於善惡的標準是浮動的。
還原生而為人的樣貌
曾為許多重大刑案被告辯護的林俊宏律師也是書中受訪者之一,他解釋,死刑案件之所以要談「求生」,辯護律師之所以必須跟檢察官比賽,正是因為被告會在新聞上、法庭上被塑造成一個惡魔,好讓大家相信被告就是一個不值得活下去的人。辯護律師的職責就是要在法庭上為被告爭取最好的保障,讓法官看到除了檢察官指出的犯罪行為以外,被告作為一個人的其他面貌,不見得有多好,但他也是一個「人」;讓法官知道一個人是基於什麼樣的因素讓他犯案當下做了這個決定。
一個人在社會上要順利生長其實要透過很多人的協助,不會只是「活下來」。面對被告也就需要社工師、心理師、犯罪學專家、被告的朋友、老師、家長讓我們了解他曾發生過什麼,這是辯護律師一直在做的事。「當這些故事看久了,就會越來越難以判斷,這個人是不是真的就只是一個惡人?心中會開始有越來越多的問號,是不是在哪裡,我們(社會)漏接了這個人?」林俊宏律師說。說服法院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畢竟能夠擔任法官、成為律師的人可能是人生相對順遂的一群,可是每個人的人生很不一樣,可能念書過程家裡突然破產,或者有各種狀況讓人頓失依靠或求助無門。像單親媽媽殺子案就是因為要同時照顧小孩的情況下,單親媽媽很難找到穩定的、好的工作,在經濟和精神壓力之下,萌生帶小孩一起離開人世的念頭。
律師從來不會去正當化被告所犯下的罪,但是被告應該要得到一個公允的評價和懲罰。書中訪談到加害者家屬,這個族群向來容易被忽視、被認為是應該被譴責的對象,林俊宏律師在律師工作中總是要透過加害者家屬來更認識被告,因此也會發現他們難以啟齒的生活壓力和困境。
司法和社會都判他死刑
長期投入轉型正義工程、2019年起擔任廢死聯盟「監所訪談計畫」外部督導的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彭仁郁老師為本書寫序,仁郁老師認為,監所中的死刑犯過的生活其實並不如外界想像,許多長期被監禁的死刑犯一心求死,活著的每時每分每秒必須面對自己曾犯下的錯誤與伴隨而來的責任,不只是司法判他死刑,而是整個社會都認為他們不值得活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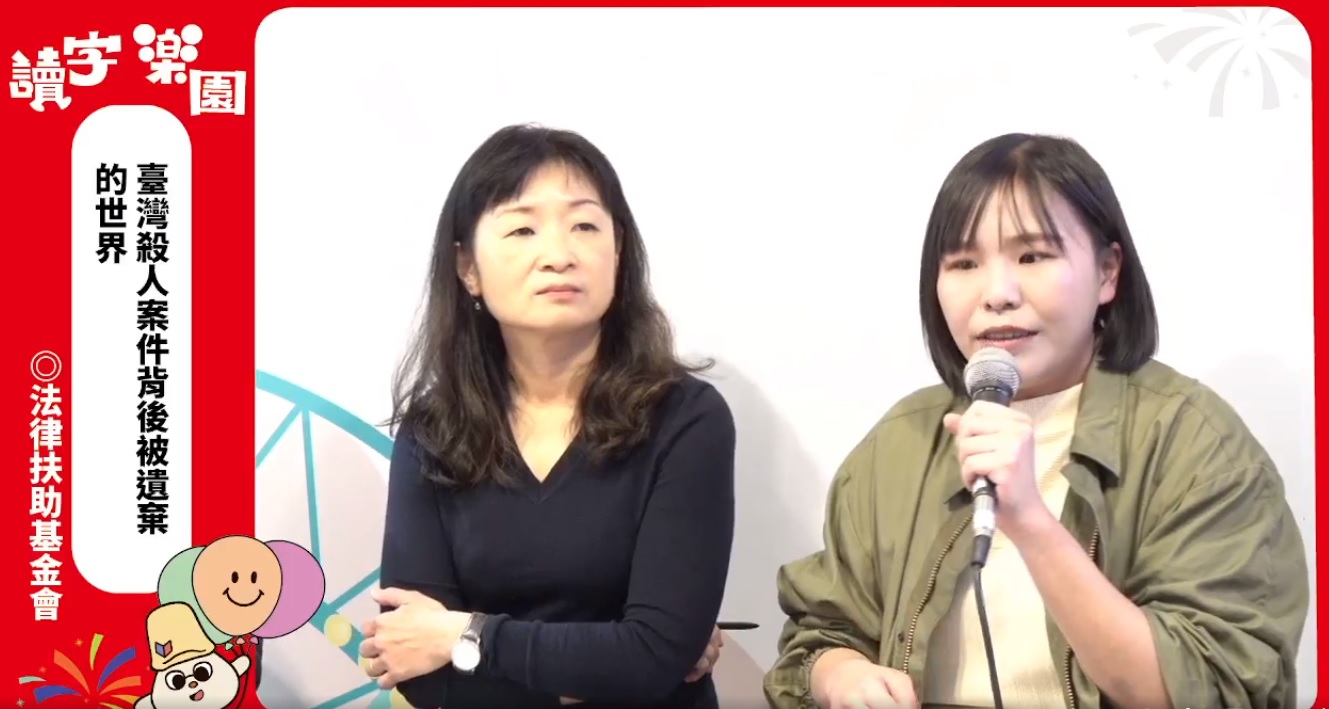
「我覺得這是一本對於殺人案件的社會心理病理解剖學,殺人這件事,不是一個人去殘害了其他人的生命而已,而是殺人事件他就是一個社會的病理現象。」仁郁老師說。
很多人會問:「為什麼要關注加害者?」我們在書中不同的篇章不斷看到有些人生命的樣態是:「我好想要好好活下來,但我沒有辦法;我每一個想要努力活下來所做的行為,都被別人當作是不值得一顧。」社會中有些人就是在我們難以想像的處境之下求生,這些人可能肉體活下來了,比如有的人從小就當焊接童工、有的人瘦到只剩下38公斤還是要養生病的孩子,就這麼撐著,但是沒有人意識到他們在成為殺人犯之前就已經被社會集體性地排除,已經在慢性地死亡。這些人從小到大都不斷經歷被否定、尊嚴遭到踐踏,當一個人的「活」沒有辦法獲得肯認時,結果就是家庭和我們的社會製造出這樣的殺人犯,很悲傷地是,我們錯把殺人當成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彭仁郁老師沉痛地表示:「我不會說每個人都要負起一樣的責任,但我會說這是我們每一個人在很多不經意的情況下,去踐踏、排除了他人之後,集體造成的社會悲劇。」
向死的欲望,是面對生存的無能手段
除了整體社會的排除以外,回到個人的層次,在心理學的理解中,每個人內在其實都有殺人衝動,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當我們看見慘絕人寰的殺人案件時,第一個非理性的反應就是反擊:也把他殺了。人類在很憤怒、絕望的情況下都會有這種衝動,但為什麼這會成為一種解法?精神分析的說法之一是,當「生」的欲望沒有辦法戰勝所面臨的困境時,「死」的欲望居然就成為了我們奪回控制感的手段。而沒有鑄下大錯的人們跟殺人者的差別是什麼?很多人有童年逆境或者生命中也遭遇過創傷,的確有許多受害者內心也存在著殺人衝動。
彭仁郁老師分享自己曾碰過有創傷的人告訴她:「如果不是來找你,我早就殺死自己、殺光我全家了,因為那樣的痛苦已經太過巨大,沒有一個人可以幫我。」我們與殺人者的差別可能在於有一個人可以接你電話、有一個人可以陪你喝酒、有一個人可以陪著你走一段路,只要有一點點連結的時候,你不一定會走到以為只有殺人才可以解決問題的那一步,「差別就在於我們擁有別的資源可以讓我們免於這樣的困境。」仁郁老師分享。
重新思索殺人案件與正義
真正的正義是什麼?如果我們認為要以殺止殺來對付殺人者的話,那我們充其量就只是報復而已。真正合乎比例原則的懲罰需要對人的處境具備想像力,法庭近年來的確也努力朝這個方向前進。而以更深遠的歷史層面來思考這個問題,倘若殺人應償命,蔣介石要背負多少條命?他羅織罪名,在沒有正當法律程序的情況下,讓上千名無辜百姓被處死。人們面對不同的犯罪案件該如何看待?在嚴重的殺人情節中,直接暴力攻擊他人致死,與蔣介石用朱砂筆批「判死刑可也」;前者的行為是在已經沒有任何手段可以展現自我意志的情況下發生,而後者批准死刑、派另一個人去執行死刑,無需承擔責任,手不沾染鮮血的暴力,至今仍未被處理面對。
又如書中所述,那些特宏興368號漁船上移工的生命、活著的尊嚴、意志力不斷受到漁業惡性循環的勞動環境消弭,這算不算是殺人?更早先為人所知的RCA工殤案,或者至今的重大工業汙染,有許多企業主明知讓勞工處於高度危險的環境、接觸可能致癌的化學物質,長此以往將危及生命,這些雇主在有意志的狀況下讓他們的勞工陷入慢性死亡的狀態,這些行為卻很難進入訴訟,甚至社會上是難以討論這些問題的。彷彿人的生命有貴賤,不易為人所知的間接殺人可以不被理會。彭仁郁老師強調,舉例犯罪事件對比並非為犯罪行為脫罪,但作為社會中的一員,我們始終必須反省思考,人與人之間關係和處境是什麼,面對重大刑案,我們能夠從中學習到什麼。
社會安全的問題總是百密一疏,但唯有當我們在願意看見社會各個角落存在著不同困境時,或許才有機會可以說,我們距離不再有人需要「求生而不可得」的世界更靠近一些。如同本書封面採用有著「悼念」花語的罌粟花圖樣,願我們能夠記憶所有因為社會生病而失去生命的人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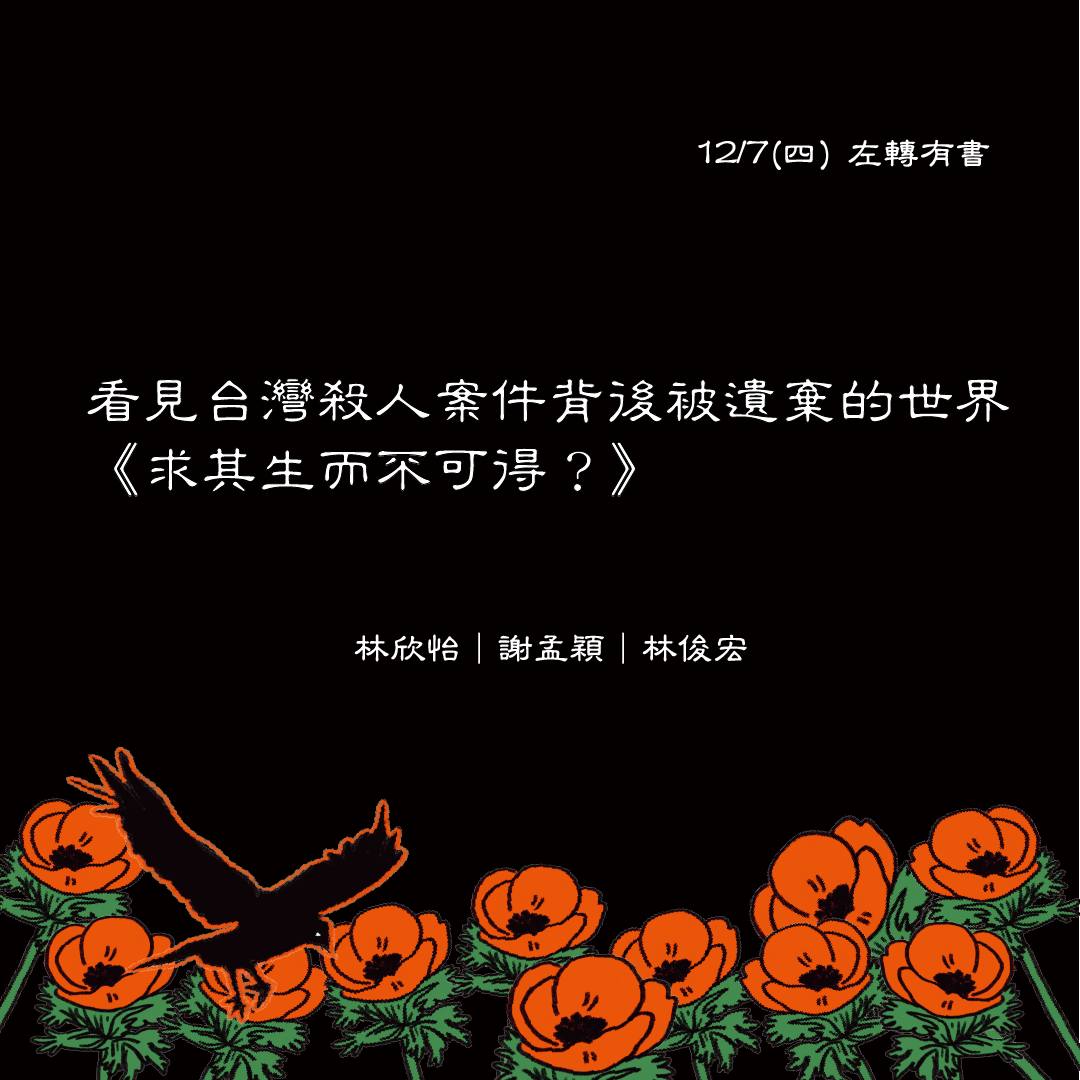
註:本文整理自【逍遙法外法律扶助跨界講座第100場:看見台灣殺人案件後被遺棄的世界《求其生而不可得?》】及台北國際書展獨立出版聯盟x讀力公民書區【看見台灣殺人案件後被遺棄的世界】兩場講座。
(編輯:林楷瀚、吳佳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