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苦,於是我們笑著說話
文/ 林安冬(廢死聯盟志工)
2018.11.22
她來信了。
自從兩年多前去看過她,她不時寫信給廢死聯盟法務主任,信中都會問候我及當初和我一起去看她的朋友。
其實我並沒有一直持續地去看她,也很久很久沒有寫信給她了。
要見她一面太難了,累進處遇第四級,她連回信給我都不被允許,她寄信的對象只能是主任。而且,我在逃避。我第一次去看她,甫離開監獄回到台中市區,在咖啡店便忍不住哭了。透過監獄接見室的透明玻璃跟話筒去認識一個新朋友,我不禁想:如果,她是自由人。
其實隱隱地會想,現在不去見她,等到某一天看到她的新聞,就是再也不可能見了。
但是想到就害怕。
我太害怕了,於是總安慰自己以後還有機會,買好了漂亮的信紙跟信封,卻遲遲沒有動筆寫信跟她說要去看她。

2018.11.23
信寄出了。請妳等我。
2018.11.29
今天監獄打了三、四通電話過來,我沒接到。剛過五點半回撥,語音說是下班時間了,我便上網查詢分機號碼。選了一個分機打過去碰運氣,還好對方接了,並幫我轉接給承辦人。她說,要我再提供一些文件資料,她才能請「編號1***」打報告,等她打完報告再讓我去接見。
「編號1***」是他們稱呼她的代號,在監獄及看守所裡面的同學,每一個都不再有名有姓,而是被扁平化成一個個編號數字,以方便管理。
我的工作有時會需要打電話去監所問受刑人的編號,我會跟名籍科報出他們的生日、身分證字號、姓名,然後得到一個編號。總覺得把人烙上編號之後,他們就變得比較不像人了,是一群棉羊吧,或是別的什麼物品。
2018.12.21
來信。她說想要貼紙,哆啦A夢的、或是史努比的。
可是雷射、螢光、浮印的貼紙都會被銷毀。她說,之前主任寄給她的那些,都被銷毀了。
「可以帶一些貼紙給我嗎?拜託。」
人要活下去,是需要希望的,生病的人總盼望好起來的那天。可是對於被判死刑的人來說,希望是奢侈的,漫漫長夜,不見天日,於是她便去盼望一些微小的東西,例如貼紙。
2018.12.22
下班後,去書局挑了很多史努比的貼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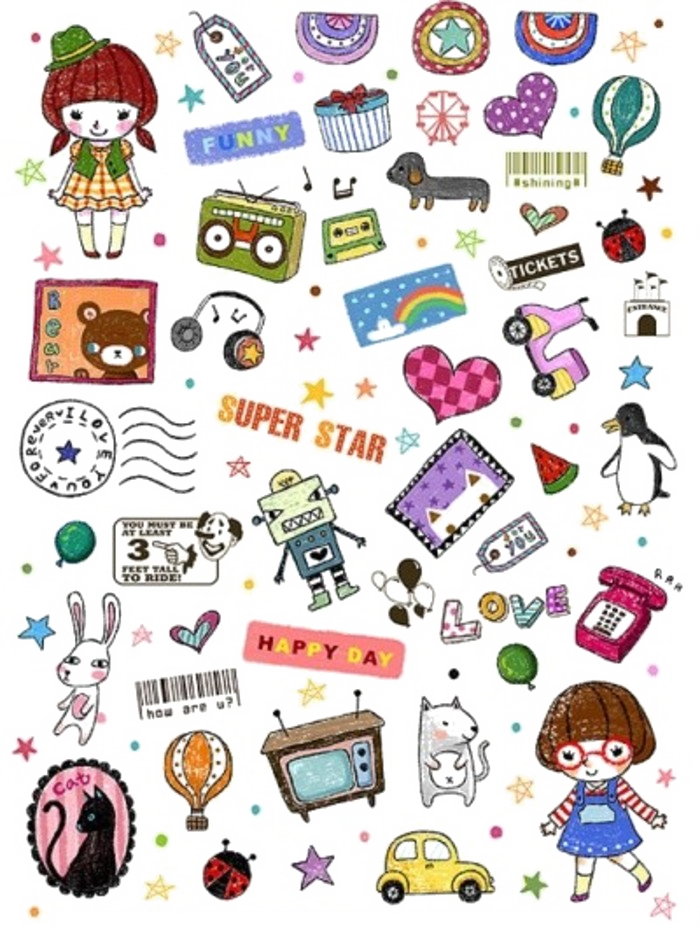
2018.12.24
早起搭高鐵。
今天的台北是陰雨綿綿的濕冷天氣,而台中則是,風和日麗的。辦理完接見的手續過後,就在座位上等待。
第四梯次。朋友問我有沒有準備好要跟她說什麼?我說沒有,她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好久不見了,妳戴著口罩只露出眼睛,雙眼皮一樣深邃,只是上一次見面的時候,妳眼角的紋路好像沒有這麼深。妳說最近溫差大,早晚差十幾度,妳怕冷,無法想像如果是在台北生活要怎麼適應氣候。
妳說我變了好多,以前還是學生樣子,現在越來越漂亮了。
為什麼戴口罩?妳說因為感冒了,裡面不能打疫苗,一間房擠十九個人,只要一個人感冒,便傳染得亂七八糟。
可以幫我買一些東西嗎?我說好。是一些保暖的衣物。在這裡每樣東西都有編號,每次代購的總價額不能超過兩千元。
通話時間剩下五分鐘。妳說,不好意思,讓妳跑這麼遠,還破費。沒有關係,妳需要什麼就儘管說。
通話時間剩下一分鐘。妳們回去小心。好。
通話時間已到。
都是笑著說的。
很苦,所以我們要笑著說話。
離開接見室,代購物品、寄了貼紙給她,外面依然是,風和日麗的。



